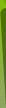秦暉訪談:什么是我們的真問題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1月26日 20:31 人物周刊 | |||||||||
|
現在學界的一個問題是,大量存在的學術泡沫,本來3000字能說清的,100萬字說得你糊里糊涂。原因之一就是無視常識 國企是誰的?當然是國民的,這有什么可說的? -本刊記者 劉天時
1月11日下午,秦暉教授坐在家中客廳沙發旁邊的矮凳上,身體前傾,一件土黃色棉布外套規規矩矩,小翻領領口露出的毛衣秋衣,層層疊疊,灰灰禿禿。在他的周圍,這個百來平米的單元房,門廳一張刨花板面的折疊飯桌,屋內直抵天棚排滿四壁的書架——有列寧全集,有女兒的照片,有會議紀念的工藝品……俗常、擁擠,不怎么個性光鮮。 而此前,在各種場合遇見過的秦暉先生,也是很容易被說成“本土”(或者“土”)的樣子:醬色的塑料框眼鏡,暗色的襯衫,下擺散著,坐在沙發邊邊上;發言也沒有“搶”啊“駁”啊的風頭,但一說就又說開了,不瞻前不顧后地,往細往遠了掰扯。 這一天,從3點到6點,他是一直在講話的。雖然感冒還沒完全好,喉嚨和鼻子還在消極怠工。 在這一大片一大片的話里面,有很靚麗很時興的詞,比如自由、民主、公正;也有些拗口的句子,比如,“一個假說被證偽,一個更完善的假說被證偽……不斷證偽的過程就是不斷接近但最終也沒法達到真理的過程”,再比如,“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大是原因”;有近在眼前的現實,比如“下崗”、“醫保”,有遠在天邊的學理,比如“羅馬法”、“嘉興藏”;……像是急切的喃喃自語,散漫里有焦灼;像是游離的廣場演說,切實里又有超脫。 而此前,對秦暉先生著說的閱讀經驗,除了“思想和理論”的學習,也補充證實著這樣的感性印象:這是位對枯燥的淵博知識、拗口的繁復道理,在行又享受的先生!人格修養上的謙卑掩映著智力上的優越;義憤害臊地躲在與價值無涉的邏輯鏈后面;責任心呢,又要固執地站到學術研討前面來;…… 關于 “心歷路程”,秦暉先生青少時代以來的回憶提供了這樣一些鏡頭: 之一,1969年的南寧,省圖書館,少年秦暉,一邊神色嚴峻地飛快翻閱,一邊如獲至寶地唰唰摘抄。時而眉頭緊鎖,時而豁然開朗。這安靜空蕩蕩的書庫外面,是一個時代的嘈雜和浮塵。 之后不久,秦暉揣著一顆15歲的赤誠之心以及一書包“如何又快又多地滅田鼠”、“如何用辣椒制作土農藥殺蚜蟲”的資料卡片,斗志昂揚地來到廣西百色田林一個離縣城100公里的村子,準備大干一場——當然,幸好沒什么實踐機會,這些浮夸時期出版物提供的“土洋結合”的農技知識,也就沒造成什么禍害。 之二,70年代初的廣西鄉下,秦暉在種田,在勞動的間隙,坐在田埂上,他準備與老鄉們“打成一片”悉心聽取人民群眾的心聲;可是他聽到的心聲,基本是張家長李家短,是黃段子是無厘頭……于是只能面紅耳赤只能耷拉著腦袋默不作聲。 “當然這不會使我‘看不起’農民,因為意識形態教育使那時的我相信這些都是‘支流’、是‘表面’,當老鄉和我談起生產或者隊里的公事時我會找到對‘貧下中農’‘本質’的感覺,更不用說假如他們‘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講些什么憶苦思甜忠黨愛國為革命種田的大道理——可惜這類‘本質’話語我從未聽到過,除了開會以外。遺憾的是老鄉們——其實我也一樣——總是生活在‘表面’而不是生活在‘本質’之中。” 之三,還是貧窮中國荒唐年代黯淡寂寞的小小村莊。秦暉在自學,農機、水電、醫藥。他鉆到拖拉機下面在修理發動機,他指指點點在修建社里的第一個水電站,他在給老鄉們開藥方……因為學農機學水電學醫藥,他又學上了電學、三角、植物分類學,因為要盡量多地參閱資料,他又學上了英文,用拼音標注的又聾又啞的頂呱呱的英文。 “那時候的學習基本是求智愛真型的。雖然學了很多實用之學,但那些年里,農村技術‘職位’也是計劃體制下按‘關系’分配的‘稀缺資源’,并不是具備有關知識者就可以此‘謀生’的。因此我在‘早稻田大學’的學習主要還是‘務虛’,是為了免于精神饑渴;低調點說,是為求知而求知,高調點說,是為追求真理——但其實也算不上什么高調,在那種環境下,除了‘真理’,你還能追求什么?” 之四,又是圖書館,這回是縣圖書館;又是如饑似渴,卻是不紅也不專的、“文革異端思想之源”的“灰皮書”,60年代為反蘇翻譯內部發行分級選閱的書。這時候的秦暉,20來歲,不時被借調到縣文化局搞民間文藝創作,于是有機會看到了“只給縣長看的書”,于是小學畢業就跟著潮流鬧革命的青年秦暉,開始了“真正的思想成長歷程”。 這之后,在鄉下鍛煉了9年之后的1978年,投考中國農民史學開創人趙儷生先生的研究生,做學生做教授,從廣西壯鄉到西安的陜西師范大學到北京的清華大學,從農民戰爭農民農村問題到經濟史到轉軌比較,從先秦到明清到當代,從“自我陶醉地”做考據派的“死學問”,到為“現實的問題與主義”,“據常識守底線”、“不得不發言、不得不辯論”……秦暉,這位先生,他的視界和聲音,“自然而然地”拓寬、“順理成章地”攪深。 “涉獵廣、專業領域淡化、逆潮流而動,但始終是有社會關懷導向的。20年來我的關注點在變化,但基本的人生態度、治學態度與價值標準是一以貫之的。它既源于一個變動社會中的求知者鑒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純粹‘興趣’:這種興趣不是為了‘學術地位’而是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轉型期一個中國公民的責任感:這個公民并無經天緯地濟世安民的‘傳統士大夫’抱負,只有一點現代國民的匹夫之責而已。” “關懷”、“責任”,在秦暉先生這里,又低調又驕傲,似乎也不大有深沉而光輝的扮相。比如,當你繼續追問: 追求“真善美”的童年期表現? ——求知欲本身是沒什么目的的。說好聽叫憂國憂民,其實就是納悶。我并沒想當什么家,只是拿到一本書,就很高興,就很喜歡看,而且這興趣是不斷轉移的,比如小學的時候,就比較喜歡天文學,有段時間還做過發電機、電動機。 能回憶起來的最早的理想? ——當時的意識形態是不提倡個人理想的。“黨叫干啥就干啥,甘當革命螺絲釘”。當時是很忌諱說當這當那的。而且我們真的也沒想,真的沒什么雄心壯志。 最早有公民概念是什么時候? ——潛移默化吧。“文革”時不也講“天下我們的天下,國家我們的國家”嗎?那時候人們還是很虛假地認為有責任感的。 內心會激蕩不安嗎?為大的問題,比如公正民主自由…… ——有。我關心的事情都是和“我”有關的,不僅僅是我研究的課題,我本身也是變革過程中的一個部分,一個主體啊。 焦慮或者憤世嫉俗嗎? ——這種情緒一直都是有的,就是不滿意唄,就是想求變求新。人之常情。 您是樂觀的嗎? ——沮喪無奈,任何時候都會有的。但我是信仰自己對自己負責的歷史觀的。中國現在的事情辦糟了,直接責任就是我們這一代人,你再往前,頂多能往前追到上一兩代人,你再把它追到孔夫子啊秦始皇啊,就沒什么意義了。這個是可以從數學上證明的。絕對的樂觀或悲觀,都沒什么根據。對公共生活的關注是每一個公民都應該有的。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非常簡單的,一個有正常智力的公民都有這個判斷能力。 …… 在天命之年,秦暉先生,在內心,在書齋,在晴冷的冬天北京,在熙來攘往的人群里,在交替的澎湃和安靜之間,一如既往地,自得其樂地,做著他所謂的“底線之上”的思想實踐——“維護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隸;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隸主;反對他人之間的強制——堅持廢奴主義。” 從歷史轉入現實 從去年下半年以來,產權改革一直是媒體報道和學界討論的熱點,您在其中的發言也比較頻繁獨到。您也談到,您在十幾年前就開始關心“分家問題”了;而在十幾年前,您為人所知是因為您在農民史問題上的研究。您最初關注轉軌是出于什么契機呢?是接待了某個上訪者,還是出于對政策研究的直覺,或者別的? 80年代我做的學問主要是農民史。我們把農民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來研究,但也關心現實的農村。在這個過程中,感到過去的一些論說有很多不能成立的地方,比如把傳統農村基本矛盾理解為租佃矛盾,用階級斗爭的理論作解釋工具;而我們試圖以比較的視角,了解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各維度,所以80年代很長一段時間,比較經濟史、現代化研究,也是我們用力的一個主要方向。不過那時侯的很多感想,基本還是以歷史研究著作來反映,不直接談現實問題。 后來,80年代末的一些事情,讓我覺得歷史和現實是打通的,歷史并沒有真正過去,我們也一直生活在歷史之中。正因為研究歷史,所以看待現實問題時才會有縱深感。比如,那段時間,有很多人認為,改革會中斷會趨于保守;但事實上,政治上是如此,但是在經濟改革上,不但沒有中斷,反而加速了。我一直就有這樣的預計,因為,道理很簡單:在沒發生沖突之前,舊體制還披著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大家長擺出慈祥面孔,子弟還要表現孝順,雖然大家已經有了很強的自我意識;但面紗被挑破了,大家都看透了,家長不能指望子弟孝順,子弟不能指望家長慈愛了。再加上,那時候,很多利益群體不能說話了,強勢利益群體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搞,一些改革就更容易了。 而且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先例。比如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以后,似乎是保守派鎮壓了自由派,但反過來,保守派在爭取自己的經濟利益方面,比自由派更自由。 凡是在這種背景下的改革都有共性:都是強勢階層推動的,缺少公共參與的空間,缺少討價還價的機制,基本上是以強權為杠桿,以既得利益為動力的。從方向上講,是進步的趨勢,但是手段缺乏公正性,在正義和道德合法性上缺失,而且會造成后遺癥。 想知道您的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您在研究農民問題時,曾經為很細節的東西,多次去云南;現在的產權改革研究呢?實地考察民間訪談多嗎? 從國內史學界講,我是最早運用基層檔案做現當代研究的。1980年代,我是陜西師范大學的老師,搞函授,跑了很多縣檔案館,那時候是沒對外開放的。檔案中有活的歷史,比如土改一段,我根據檔案的線索,找到了當事人做訪談。后來到了北京,參與組織了一些農村調查,并與改革機構有過比較密切的合作,另外還有一些國際交流,實感就更多了。 在研究方法上,我想強調的一點是,普遍的問題是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脫節,要宏就一直宏下去,要微就一路微下去,兩者不能形成認識循環。我想更好的方式應該是這樣:宏觀研究從認識論上,應該提出具有明顯的邏輯嚴謹的理論框架,因為邊界清晰,或者可以證實或者可以證偽,形成啟示,引向微觀問題的關注;而不是,宏觀含含糊糊,大而無當,看似什么都能解釋,實際上什么都解釋不了。我覺得應該是,宏觀理論促使微觀研究,微觀研究對宏觀理論研究證偽,然后產生第二代的理論,從而形成知識的循環。 在這一點上,我一直遵循我研究生時代的導師趙儷生先生的教誨,按他的說法是:小問題越做越大,大問題越做越小。既要避免宋學傳統的空疏,又要避免漢學傳統的豆丁。 您在做企業轉制研究時,與企業工人、管理層的實際接觸,對您的研究重要嗎?會有上訪的人向您求助嗎?有哪些技術幫助您把握案例研究中的客觀性? 會有接觸。我講的問題,基本都是有經驗基礎的,但一般不直接介入案例,那樣會陷入是非。我的研究是,把案例歸納為問題,進而理論論述。其功能,在于提醒相關的注意,注意存在的問題,具體解決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在采集事實時,會盡量從各個不同角度。而且我也相信: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中,每個人都不能標榜自己絕對客觀,但是在主觀上要有追求客觀的愿望。只要有這個愿望,看問題即使是有價值取向也問題不大,因為不同的價值取向可以互補。任何人類知識的增長,都是通過深刻的片面性互相補充完成的。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有一個自由的開放的探討問題的機制和環境。 整天收到類似的來信,多極了。但我的身份其實只是學者。 中國人缺少邏輯能力? 可能因為您的觀點,您一貫的姿態——強調改革的公正公平,申張弱勢群體的權益,讓大家對您的影響力的期待,不僅僅限于一個學者…… 作為學者,我并不認為我主觀上有很強的為某一個群體說話的沖動。我不是政黨領袖,也不需要爭取選民,所以沒這個動機。我寫,當然是有我的價值關懷在里面;但我還是試圖邏輯嚴謹、有事實根據。但是,還是有沖動的,還是有感而發的——在有據而論的基礎上。 至于影響力,我想是,盡人事,由天命。這個應該不是我主要考慮的東西。我既不是冷漠的,也不是單純地喜好感情宣泄。我做的事情,什么性質,很難說。什么是學術呢?我想,第一是有實證基礎的,不是創作;第二,在實證基礎上形成思想,邏輯上是嚴謹的,帶來知識增量,擴充人們的認知領域。現在學界的一個問題是,大量存在的學術泡沫,本來3000字說能清的,100萬字說得你糊里糊涂。原因之一就是無視常識。 “常識”也是您經常提到的一個詞,您有一篇文章題目是《在常識之上思想》。您確實覺得我們處在一個常識被遮蔽的現實中嗎? 有些很簡單的問題是被復雜的語言說亂套的。比如,國企是誰的?當然是國民的,這有什么可說的?但是有人就說了,國企本來就不是大家的,國企是法人的,似乎法人可以是脫離自然人存在的一樣——其實人所共知,法人背后是必然有自然人作基礎的;還有人說國企是無主物,可是我們都知道,如果你私拿了,就會被認為是貪污,如果是無主物,按羅馬法,發現者所有,是非常正當的;還有人說國企沒有效率,沒有效率就可以給私人嗎?邏輯上說不通啊;還有說,本來就是搶的不義之財,現在就要還給資本家,但如果是不義之財,就應該還給“那個”資本家,而不是抽象的資本家階層,你如果從甲搶來的東西還給乙,那是雙重的不公正。 反過來說,因為改革過程中的不公正,而否定國企改革的人,也違背常識和邏輯。比如說,郎咸平說,誰能證明國企比私企沒效率,你給我拿出數字來。這還用拿數字嗎?既然你在那大聲說國資流失,既然國企連照料資產都做不好,還怎么談更有效率呢?而且我們說有無效率,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充分競爭的情況下,但國企,很多都是壟斷,壟斷就談不上有無效率。 那您覺得為什么“我們這么沒有邏輯”?是智力、或者中西文化上的什么差異嗎? 不能這么說,并非中國人就缺少邏輯能力,很多情況是背后有太多的利益推動,有意忽略罷了。比如說,現在很多人都在用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成本的降低”為用專制手段私自處置公共資產的行為辯解,說,不允許各階層談判、掌權人任意處置,可以有效地降低制度變遷的交易費用。作為事實,是有的,但合理性何在啊?這和科斯(注:交易理論提出者)講的是兩回事,他說的是企業節約交易費用,他沒說強權可以節約交易費用,也從來沒認為可以通過剝奪人們交易權利的方式降低交易費用,科斯的節約交易費用,是在人人有充分交易權利的前提下提出的。如果按照這種強盜邏輯,奴隸制是最能節約交易費用的,因為我把你的交易權利剝奪了,你就不交易了,那不就最省了嗎?比如古拉格群島,那還真是最節約交易費用的。 您的文章中經常會提到這個是“假問題”、那個是“偽命題”,您似乎費很大力氣在做澄清工作。 是啊。比如在東西問題上,我就覺得有一種偏向就過了,就一直在回避真問題。這個偏向過分強調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好像西方人和中國人有什么天然不同的價值追求,好像西方人就更愛自由,而東方人就喜歡有一個大家長管自己。哪有這回事?那為什么外國的監獄中國的監獄都要上鎖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自己原來也有似是而非的時期,也寫過,“中國人害怕風險,西方人愛好冒險”之類的文章。但我現在覺得,中西差異的真正所在是,人們面臨的現實的問題有很大差異,中西交流的隔閡,并不在文化。 政府的權利和責任 關于目前中國需要左派還是右派,是社會民主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學界爭論得很熱鬧,而您似乎對這兩方都有不滿不屑,甚至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假問題。 就本意而言,自由主義是關于限制政府權利的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是關于強化政府責任的主義,本來是不相沖突的。也就是自由主義從來不會直接講政府不負責任,民主主義從來不講政府可以為所欲為權利不受制約;但是因為權利和責任在憲政框架下是統一的,你講責任大,你就得承認他的權利大,你講權利小,你就得承認他的責任也小點。所以就形成對立了。因為作為統治者,當然是想權利大責任小,為所欲為,想搶什么搶什么,同時對你的死活不聞不問;對老百姓講,正好反過來,一方面希望權利意義上的小政府,盡可能的多自由,又希望是責任意義上的大政府,盡可能的多福利。但是魚和熊掌不能兼得,所以憲政解決的就是這個責權對應的問題。 但在此、在憲政之前,你完全可能面對一個責任小權利大的政府,那么你面對這樣的政府,你可以同時要求,一方面限制政府權利,一方面追問政府責任。也就不存在大小政府的爭論。大政府還是小政府,自由多些還是福利多些,就現在的中國,當然是假問題。真問題的雙方是這樣構成的:以“限制政府權利擴大責任”為一方,以“推卸政府責任擴大政府權利”為另一方,我們要面臨的是這樣的選擇和分野。這是“是否要追求一個責權對應的政府”的問題;是“是否保障公民基本自由民主權利”的問題;是否堅持底線的問題。 既然您近年來研究國企轉軌問題,能否就我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做一個概括性的描述? 現在的中國并不是完全自由市場經濟,這個情況下,排除政治因素的階級分析不大可能。中國的現實是,單位不同,同樣是工人,狀況可能很不一樣;企業家也是,有權力的和被權力勒索的,處境很不同。但中國目前,在現階段改革過程中,無權勢者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秦暉底線 秦暉曾多次針對國內學界“自由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爭論,斷然指出: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時代,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有很大的價值重合。我們應該共同對付反自由主義、反社會民主的民粹主義與專制主義;共同追求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贊同的基本價值,比如基本公民權利、自由與程序正義。這是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而并不是什么兩個主義“之間”的“第三”立場。 秦暉思想關鍵詞 關于產權改革 賣方缺位 一項資產面臨處置,但是沒有來出賣的人,也即所有者缺位。 看守者交易 國有資產法理上屬于“國民”,政府只是看守這些資產。政府卻利用權力對其進行處置。 界定式私有化 所謂“界定”,說穿了就是行政劃撥。由于國有資本存量太大難以賣掉,就干脆采用劃撥方式徑自將其從“國民所有”“界定”為內部人所有,在內部人中又指定老板拿大頭。 經營者持大股 在股本設置時,向經營層傾斜,鼓勵企業經營層多持股、持大股,避免平均持股;鼓勵企業法人代表多渠道籌資買斷企業法人股,資金不足者,允許分期付清(亦即可以以未來紅利沖抵)。在以個人股本作抵押的前提下,允許將企業的銀行短期貸款優先劃轉到企業經營層個人的名下,實行貸款轉股本,引導貸款擴股向企業經營層集中。 內部人私有化 以長沙湘江涂料為例。只把17年前的或企業創建時的初始投資算作國有,而以這些投資為本滾動產生的“積累”都被“界定”為內部人(“企業集體”)資產。這樣“界定”,80%的企業資產便從“國有”帳上消失并轉入內部人手中,再經“優惠”贖買,余下的20%國有資產比率又縮水成了6%,連同未進入新企業資本帳內而是上交財政的贖買金,共為12%,亦即88%的原來人們心目中的國有資產“在10天左右時間里”都被大筆一揮“界定”掉了。 關于中國道路 中國原始積累的方式 中國權貴資本在一開始民間經濟貧瘠的情況下,主要靠的是從國庫中挖資源。現在國庫漸漸挖得沒什么了,就逐漸轉而把國庫當成一個中轉站,通過國庫去挖民間的資源。一方面“化(平民之)私為公”,另一方面“化公為(權貴之)私”。 中國可能面臨的危險 歷史上反民主的寡頭主義與反自由的民粹主義往往互為因果,造成“不公正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正”之惡性循環。這正是中國目前面臨的巨大風險。 中國應該走的道路 假如中國在如今經濟周期的增長活躍階段,不失時機地啟動民主進程,許多矛盾可以由于“蛋糕不斷做大”而緩解,因民主化而帶出“矯正正義”的問題還是相對容易解決的。 秦暉 生于1953年,現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后首批碩士畢業于蘭州大學,曾任陜西師范大學教授(1992年起)、中國農村發展信托投資公司研究員(1994年),現為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理事、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方法》、《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等學術刊物編委。 1980年代初主要研究農民史,后期轉向經濟史研究,90年代致力于結合歷史研究與現實研究,在結合社會調查與歷史文獻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農民學,并主持了一系列鄉村調查,主編了《農民學叢書》。近年開始中國與東歐的轉軌比較研究,關注國企轉制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弱勢者權益受侵害的問題。 主要著作:《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市場的昨天與今大:商品經濟、市場理性、社會公正》、《實踐自由》等。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學人 > 經濟學人--秦暉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4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