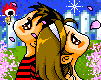| 《行政許可法》:兩難中誕生的次優選擇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28日 11:15 《商務周刊》雜志 | ||||||||||
|
——專訪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教授、國家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專家咨詢組成員周漢華 ●我們之所以出現一部其他國家都沒有的《行政許可法》,是希望通過它來界定清晰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來保證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當中起到更基礎的作用 ●我們沒有時間去等待一個漫長的過程再形成一個制度。事實上,許可法面臨的某
●從清末戊戌變法開始,中國一百年的變法,成功的少,失敗的多。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不光對《行政許可法》的實施,對我們變法的模式,對我們整個法治現代化的模式,都要保持一種清醒的頭腦 ●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有一個前提條件——必須要解決公眾參與和民主的問題。因為沒有一個民主的制約機制,行政權力就會在“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中搖擺 □記者 任雪松 自7月1日開始,中國地方政府部門掌管審批權力的“紅色圖章”被戴上了一個“緊箍咒”:官員們在行使這一權力時都必須在最新實施的《行政許可法》規范下小心行事。而這部法律也使中國成為世界首個為“行政許可行為”單獨立法的國家。 行政許可也就是普遍意義上的行政審批。此前,行政審批的權力體現在各個政府部門密密麻麻的“紅色圖章”以及“紅頭文件”之中,甚至公民步入婚姻殿堂都得需要多個政府部門的許可。 藉《行政許可法》的實施,中國各省市立法部門著手對當地的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進行修改和廢止。北京市在不久前廢止了《北京市外地來京人員務工管理規定》等28項政府規章,上海市則有100多項行政許可事項在7月1日前被取消,這些事項都涉及經濟、城市建設、社會管理等多個領域。 除了對龐大繁雜的法規進行清理外,中國人事部還責令全體國家公務員參加《行政許可法》培訓和考試。像學習黨的“三講”一樣,各級政府部門也正在掀起學習《行政許可法》的高潮。 諸多矛盾都顯示,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國需要對于早前模糊的政府權力邊界進行重新界定。此前,中國僵化的行政審批制度引致腐敗、政府管制、行業壟斷等諸多問題。按照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汪永清的說法:“問題之一就是政府管得太多,政府越位、缺位、錯位現象突出,但同時政府應該履行的職責又沒有履行好。” 那么,政府應該如何劃定自己的權力邊界?此前中國管得太多、權力太大的全能型政府與《行政許可法》所意指“有限政府”究竟有多遠?《商務周刊》就此專訪了參與《行政許可法》起草制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周漢華教授。 《商務周刊》:有人說,中國的《行政許可法》是世界第一部行政許可立法,那么,為什么中國需要制定這樣一部法律? 周漢華:這里有一個大的背景,要從中國法治推進的方式,或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模式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區分談起。西方國家的法治是自發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經過幾百年(市場經濟和法治是同步發展的),甚至是上千年的歷史發展形成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法律制度也是順其自然發展的過程。比如在政府許可層面,哪些領域設許可,哪些領域不應設許可,如果設許可怎樣設條件等等,都是在漫長的過程中,一個個具體領域自己發展起來。 中國則是一個變法模式,和西方的自發模式不同。我們是要造就一個法律的體系,讓這個法律體系來推動市場經濟的形成,所以我們叫變法、改革。所以實際上中國法律的發展和市場的發展在一定的程度上說是雙軌的,并不是同時進行,當市場結構尚未發展到某一程度的時候,我們通過變法,制定新的法律,推動產權結構的改造。這種變法的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有時候,法往往走在現實生活的前面,而法律經常被當做一種推動社會變革的工具,通常發展中國家都會面臨這種情況。 此外,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進程要求我們必須在相對比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法治體系的構建,在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時間,按照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要在2010年之前基本建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這是一個法治驅動型的模式,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的法律體系來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就是把人家在兩步里要走的路放在一步里走,就是必須把別人花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的東西,我們通過一部法律來把它推動出來。像產權制度改造、公司法的形成,以前公司的設立需要國家特許,西方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沉淀才形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現代公司制度。 許可也是一樣的,我們希望通過一部許可法來界定清晰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保證市場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更基礎的作用,就出現了其他國家都沒有的一部許可法。 其他國家為什么沒有這樣一部行政許可法律,我跟很多國外專家探討過這個問題。他們回答了兩點。其一,沒必要,因為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是經過一個相對漫長的自然演化過程形成的,在每一個領域里面都形成了一套相應的法律制度。比如,日本經過改革后有1萬多項行政許可,韓國經過改革后還有6000多項,在美國,開理發店還需要許可,此外,還有釣魚法、煙酒銷售等細枝末節的許可,所以他沒有必要經過一個整齊劃一的法律來規范所有不同領域的行為。其二,他們認為行政許可事項異常復雜,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所覆蓋的領域差別太大,所以他們不會做這樣一部一刀切的法律,也認為不太可能做成,所以他們就沒有這樣一部許可法。英國、澳大利亞在2001年也分別制定了一部法律,名字也叫許可法,但他的許可法講的是特種娛樂場所的許可法,比如煙酒的專營等等,是非常有限的。像我們這種適用于所有政府審批事項的,世界上獨此一家。 《商務周刊》:有中國特色的許可法,這聽起來似乎難以讓人信服。 周漢華:但中國必須這么做,因為中國必須要通過一種變法模式來推進法治的形成,我們不可能像西方一樣經過幾百年再來進行規范。為什么呢?比如,我們的腐敗非常嚴重,我們已經不能再那么等下去了,我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已經嚴重影響到市場機制的形成,我們也沒有時間去等待一個漫長的過程再形成一個制度。 事實上,許可法面臨的某種程度上的兩難境地,也代表了中國現代化的一種困境,后發國家的現代化共同面臨一種這樣的困境。我們政府的改革已經遠遠落后于市場化改革,政府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市場改革的障礙,不實質性地約束政府的權力,那么就會給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構成很大的阻力。但反過來你要制定,就是我們剛說的這種一刀切的變法模式,相應會帶來很大的社會成本。更大的問題就是,在法律實施當中,可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就像中國的環境立法,我們國家的環境法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環境法相比都毫不遜色,世界上所有先進的環境制度、環境觀念,我國的環境法里都有,但是我們的環境法在實施當中卻不盡如人意。我國的在環保領域的投入所占GDP的比例超過了1.5%,已經達到1.55%。在國外,GDP的投入超過了1.5%是環境好轉的一個門檻,但我們在日常環境中并沒有感到有什么好轉,國家環保局對環境的評價是,基本遏制了環境惡化的傾向。這就是這種變法模式的兩難境地——不得不做,但它又會有很大的社會成本,會面臨很多的問題。 《商務周刊》:這的確是一個兩難的選擇。《行政許可法》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界定政府權力邊界的問題,而如何界定政府權力邊界,似乎也是一直困擾政府的難題。為什么此前政府的行政職能、職權容易發生逾界行為?深層次的根源是什么? 周漢華:正如你說的,審批權是一種能夠給審批者帶來實實在在利益的一種權力,人們常說,在政府機關有幾種權力是必需搶的:一項就是審批權,一項是處罰權,還有一個就是法律解釋權,這被稱為新的“三權分立”。搶到的權力在實施當中如果不受到限制,就必然會加大交易的成本,導致政府的腐敗。 許可法的醞釀應該說是從1996年就開始了,從全國人大到法工委,再轉到了全國法制辦。我們可以看到,1990年代中后期典型的腐敗案例,幾乎都是與行使許可權、審批權導致的腐敗相關的。比如1990年代末期湖北康賽上市腐敗案,就因為當時每個省部級的單位都有兩個上市的指標,所以一些企業為了上市,就去打通這些手里有上市指標的省部級單位。而當時全國出現一大批體改委系統的主任落馬案件,幾乎都和他們行使審批權有關。 顯然,大批官員的腐敗落馬現象,已經到了危及政府的權威,危及市場化改革進行的地步。事實上,在深圳等地方政府,已經出現自發探索行政許可、審批制度改革的行為,以提供一個更優的投資環境。而在中央政府層面上,為解決腐敗痼疾而進行的審批制度改革是制定《行政許可法》一個重要的考慮。此外,這還是為適應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政府的權力過大,對市場干預過多,不符合世貿組織的要求。 《商務周刊》:是不是政府作為行政管理部門行使行政權力的合法性需要確認?以前實際上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周漢華:的確,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在許可的設定權上沒有規范。誰都可以來設定許可,政府機關可以設定許可,行業組織也可以設定許可,甚至一些社會組織也可以設定許可,存在一種許可的泛濫。本次許可法的制定實施,在許可的設定權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不是誰都可以設定許可的,只能是法律規定的那幾類特殊的主體。這次的收權是收得比較緊的,因為現在能設定許可的有全國人大、國務院、省級人大和它的常委會。 另外,從許可的實施上看,原來不光是誰都可以設立許可,而且誰都可以實施許可,授權行使,委托行使滿天飛。《行政許可法》對此做出了嚴格的規定,許可的實施原則只有行政機關可以,而委托實施,只能在法律規定范圍委托給下級行政機關實施,從而避免出現滿大街都是執法人員的現象。 《商務周刊》:許可法的法律條文非常詳實,非常深入,它從法律層面對政府行為做出了規范和制約。但其現實的操作性如何?一種擔心是,中國歷來都是一個行政權威凌駕于制度權威的國度,如何使《行政許可法》不會淪為“花瓶”的境地? 周漢華:《行政許可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相關的法律,一共83條,幾千個字,但在實施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這部法律會不會只是白紙黑字停留在紙面上?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對于后進發展中國家而言,現代化的準備過程,即法治的整個過程就是一個高風險的過程,如果我們僅僅去看法律條文,發展中國家可能毫不遜色,甚至在很多規定上比很多發達國家還要現代,但剝開法律規范層面,在社會現實中的法律實施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卻差得很遠很遠。我們現在的法治會面臨同樣巨大的挑戰,也有可能在實踐當中遇上各種各樣的阻力。這并不奇怪,因為這是我們變法模式本身所決定的。 從清末戊戌變法開始,中國一百年的變法,成功的少,失敗的多。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不光對《行政許可法》的實施,對我們變法的模式,對我們整個法治化的模式,都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把困難想的多一點,是一種正常的思維方式,也是一種理性的思維方式。 許可法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相應的也有一些制度設計,但它能不能最終順利的實施,既要看許可法本身的制度設計有沒有起作用,更重要的也取決整個社會條件是不是能夠對它的順利實施提供一個平穩過渡的機會。從它自己內在的規定來說,有些機制可以保障它的實施。比如,現在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實施《行政許可法》的一個司法解釋,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因為許可法的實施最終要通過司法途徑來解決的。原來的司法解釋都是在法律實施很久之后,出現很多問題之后,才會出臺司法解釋,這次最高人民法院提前介入的這種積極態度本身說明:許可法實施后,如果行政機關違反了許可法的規定,公眾訴諸法院,最高法院已經做好了相關準備來受理這些案件,并對違反許可法的行為做出審查,這是一個重要的制度保障。 此外,國務院為了貫徹實施許可法,提前7、8個月把省部級的一把手召集到北京來開會,對部省級的領導進行專門培訓,在我們國家為一部法律這么做尚屬首次。 但現在影響到許可法實施的因素也有很多。第一,中國當前整個社會結構與許可法所追求的更多讓市場配置資源的“有限政府”還有相當的距離。我們現在的社會結構很大程度上還沒有完全擺脫行政權力主導,行政機關權力過大,一些地方政府領導人還是立足于“管”,在這種思維定式之下,《行政許可法》所體現的有限政府的理念、市場優先等先進理念能否實施需要經受考驗。 第二,想通過《行政許可法》的幾千個字來替代此次清理出的涉及社會經濟生活各個層面的4000多項政府審批權限,顯然會面臨著法律本身的缺陷。法律規定的是高度原則性的,對某些具體情況不能考慮的過分細致,所以在實踐當中,《行政許可法》的落實會受到巨大的挑戰。 第三,利益集團的重新調整。許可涉及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不光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還涉及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甚至會涉及一個政府內部不同司、局之間的關系,不同人之間的關系。它是一次劇烈的利益重新調整的過程。 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行政許可法》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實施機關。一定要有一個權威、高層次的公立機構來保證和推動許可法的實施。我的建議是國務院法制辦、國家發改委、監察部包括國務院發展中心進行整合,形成一個對國務院直接負責的實施機構,通過這么一個辦公室對許可的設立,成本效益問題,定期的評估等等進行集中的審查,就像美國的OMB(管理和預算辦公室)。 《商務周刊》:《行政許可法》把便民作為立法中最重要的原則之一,使這部法律充滿了親民色彩。但在當前的中國,官、民在一些利益格局中的沖突矛盾比較激烈,《行政許可法》能否從根本上調和這種利益沖突? 周漢華:在服務型政府方面,《行政許可法》的理念是比較先進的。政府和公眾本來是處于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而服務型政府主要體現在程序上,即在管理與被管理的過程中體現服務型政府的觀念。許可法中服務性政府的理念體現在每一個程序上,從許可的申請到行政機關的受理,到行政機關做出決定,到行政機關最后進行監督檢查,每一個環節都對行政機關制定了非常嚴格的規定。這樣就保證了服務型政府不會僅僅停留在口號上,而是體現在實實在在的每一個執行環節當中。 《商務周刊》:一些地方和部門利用行政許可搞地區封鎖、行業壟斷,妨礙統一市場的形成和公平競爭,這種情形我們早有關注,今年宏觀調控中面臨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利益沖突明顯,地方政府的利益沖動很難遏止,《行政許可法》實施后,對此會產生怎樣影響? 周漢華:《行政許可法》一個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在中央政府的權威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當中求得一個平衡。在維護中央政府權威上,此次的許可法走到了一個立法的新高度。2000年的《立法法》,是肯定了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以及國務院政府部門規章的法律效力,而此次《行政許可法》在中央政府權力上收上是做的非常徹底的。其對地方政府行政權力,甚至部委的權力都做出了相當的限制和上收,省級政府以下的行政部門現在已經不能自行設立行政許可和審批,即使是省級政府,也只能做一年的臨時性許可。這在強化中央權威,打破地方保護主義上是從未有過的。不管是在權力的范圍上,還是在權力行使的正當性上,許可法都體現了中央政府維護法治統一的決心。 此外,許可法也希望能夠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中國的一個省甚至比一些國家的規模大得多。比如,對于經濟類的行政許可,省一級政府報國務院批準,可以在本省范圍內停止某些許可項目的實施。 但對于實現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我本人并不像轉型服務型政府一定能實現那樣樂觀。因為許可法對于服務型政府在程序和制度設計上有著一系列的保障,但如何做到行政權力“收而不死,放而不亂”,尺度難于拿捏。尤其中國當前已經存在比較嚴重的地方分割問題,有必要更多地強調中央的權威、法治的統一。但又要認識到中國各地方的情況千差萬別,中國很多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的,是在地方力量的驅動下進行的改革,所以怎樣在維護中央權威、法治統一的過程當中,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創造性,而不是過于強調中央的權力上收,在權力的收放之間做文章,這是一篇大題目。 其中的困境在于,從世界發展的潮流和信息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各國都是強調一個網狀結構、扁平結構,以減少決策的層級,地方分權是現代化發展的必然潮流。但在《行政許可法》的實施上,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權力上收,還有垂直管理,這似乎與各國發展的潮流是相悖的。吳敬璉老師也認為,在中國這是不得不做的選擇,因為中國沒有形成一個對于行政權力的有效制約結構,或者說,我們還沒有形成一個憲政體制。放權的前提條件是地方政府對人民負責,但我們現在向地方分權,很多情況權力分到地方官員個人手里去了,地方官員利用這種權力去牟取個人利益,比如批地,經營城市,自己中飽私囊或為政府謀福利。利益并沒有下放到地方老百姓的頭上。所以,才會出現現在的權力上收、宏觀調控。 這為我們提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有一個前提條件——必須要解決公眾參與和民主的問題。因為沒有一個民主的制約機制,行政權力就會在“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中搖擺。 事實上,在形成民主約束之前,地方分權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從中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來看,地方政府行政分權,有利于地方政府之間開展競爭,在地方政府的多元競爭當中,提高公共產品的服務質量。 有兩個思路解決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一個是從根本上解決,就是推動民主建設、憲政建設,這樣才能跳出惡性循環。而在建成這一良性體系之前,我們的過渡階段也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經濟時評 > 《商務周刊》2004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