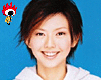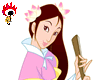| 批評規(guī)則、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6月13日 20:07 中評網(wǎng) | |||||||||
|
張曙光 1.引言 去年上半年,何清漣女士的大作《現(xiàn)代化的陷阱——當(dāng)代中國的社會經(jīng)濟問題》(中國經(jīng)濟出版社,1998;以下簡稱《陷阱》;凡引自該書,只注頁碼)一書出版,風(fēng)入松書店
回國后不久,我去中國政法大學(xué)作“經(jīng)濟學(xué)(家)如何講道德?”的學(xué)術(shù)講演。一學(xué)生問我,近半年來,《讀書》接連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圍繞著何清漣的《現(xiàn)代化的陷阱》和樊綱的《“不道德”的經(jīng)濟學(xué)》(1998)等,形成了“現(xiàn)實派”和“學(xué)院派”的激烈爭論,你對此有何評論?筆者作了回答。回家后,憶及當(dāng)時的答問,自我感覺良好,隨將學(xué)生的提問和我的回答打電話告訴汪丁丁博士,丁丁認為我的回答不錯,很有意境,建議我將此寫成文章。這就是本文的由來。 2.“現(xiàn)實派”和“學(xué)院派” 有關(guān)這一問題的提法是姚新勇先生概括出來的。他在《讀書》上著文(1998,以下簡稱《姚文》)說,近幾年來,在經(jīng)濟學(xué)圈內(nèi),“存在著一場未直接挑明的爭論,其代表人物一邊是何清漣,一邊是所謂“過渡經(jīng)濟學(xué)派”的學(xué)院派人物,如盛洪、樊綱”。《姚文》對后者有明確的稱謂:“學(xué)院派”;對前者沒有。這有些不公。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依據(jù)他的描述,把前者稱為“現(xiàn)實派”,以便與“學(xué)院派”相對應(yīng)。 什么是“學(xué)院派”?《姚文》是如何使用“學(xué)院派”這一概念的?弄清這一點,也許是我們解開這一問題的關(guān)鍵。 據(jù)《辭海》稱,“學(xué)院派”亦稱學(xué)院主義。是17世紀在歐洲各國官辦美術(shù)學(xué)院中形成的流派,以保守、陳腐的觀點,從基督教傳說、神話故事中吸取題材,或畫阿諛當(dāng)代權(quán)貴的作品,在藝術(shù)上采取死板的格式,追求繁瑣、浮華的細節(jié),以“古典傳統(tǒng)”的維護者自居,排斥其他藝術(shù)派別的創(chuàng)造與革新,直接為封建貴族或資產(chǎn)階段政治服務(wù),或迎合其欣賞趣味。 與“學(xué)院派”相近的一個概念是“經(jīng)院哲學(xué)”。在“現(xiàn)實派”和“學(xué)院派”未直接挑明的爭論中,秦暉即卞悟先生(同一篇文章,在封面上印著作者的名子秦暉,但在目錄和正文中卻以筆名卞悟署名,此乃《讀書》之誤;1998,以下簡稱《秦文》)也提到了這個概念。對此,《辭海》也有一個解釋,現(xiàn)抄錄于此:中世紀歐洲主要哲學(xué)思想的總稱,因產(chǎn)生于天主教的學(xué)院,故而得名。主張理性服從信仰,哲學(xué)是“神學(xué)的婢女”,目的在于論證基督教的教條,維護教會和封建主的統(tǒng)治。轉(zhuǎn)義為任何繁瑣的哲學(xué)或理論,大部分研究脫離現(xiàn)實的抽象概念,論證方法甚為繁瑣。 《辭海》的解釋非常清楚,用不著再畫蛇添足。《姚文》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和運用的,并且是在與“現(xiàn)實派”的比較中闡述的。按照《姚文》的說明,《陷阱》的作者“相當(dāng)直率地揭示了”中國社會中“日益惡化的諸多結(jié)構(gòu)性矛盾”及其產(chǎn)生的根源,“語言平實,道德關(guān)懷溢于言表”。而“學(xué)院派”則大不相同,他們的文章“太深奧,外行人無法看懂”;他們“生搬硬套西方的經(jīng)濟學(xué)理論,脫離對具體改革實踐、問題、矛盾的分析,以學(xué)術(shù)純粹性、客觀性的外表,掩蓋其理論和道德的雙重矯情”,“放棄了理論對現(xiàn)實的批判性,落入對主流政治的一味盲從”。進而,《秦文》從股份合作制過程中“分”與“賣”兩種產(chǎn)權(quán)改革方式的討論中推導(dǎo)出“反對民主私有化而倡導(dǎo)權(quán)貴私有化”的政治結(jié)論。 改革開放以前,由于思想禁錮,輿論控制,中國經(jīng)濟學(xué)處于一家獨尊的狀態(tài),雖然也有一些不同意見的爭論,但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形成不同的學(xué)術(shù)派別。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思想解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的經(jīng)濟學(xué)研究也出現(xiàn)了繁榮的局面,并且由于經(jīng)濟建設(shè)實踐的需要,經(jīng)濟學(xué)也成為顯學(xué),但是,由于基礎(chǔ)較差,知識積累不足,再加上經(jīng)濟學(xué)家的訓(xùn)練不夠,雖然出現(xiàn)了一些不同的經(jīng)濟學(xué)論壇,但還沒有形成獨立的經(jīng)濟學(xué)派別。這并不是中國經(jīng)濟學(xué)家的光榮,而是令中國經(jīng)濟學(xué)家報愧的事情。但是,有關(guān)“現(xiàn)實派”和“學(xué)院派”爭論的說法,卻并不鮮見。想當(dāng)年,我們曾經(jīng)把胡適作為“學(xué)院派”的代表大加批判,同時也否定了他在學(xué)術(shù)上的貢獻。“文革”前后,張聞天和孫冶方等老一代經(jīng)濟學(xué)家曾被當(dāng)作“不食人間煙火”的“學(xué)院派”,進而被打成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一些老教授老專家也從“學(xué)院派”和“經(jīng)院哲學(xué)”的代表而變成了“反動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總之,在中國,“學(xué)院派”通常是與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封資修等連在一起或者齊名。我想,這段歷史大家不會忘記。因此,筆者對于在學(xué)術(shù)討論中作政治批判,隨意給別人扣上“學(xué)院派”和“經(jīng)院哲學(xué)”之類的政治帽子的作法,不僅不能贊同,而且表示反對。這會毒化學(xué)術(shù)氣氛,不利于學(xué)術(shù)討論的正常開展。 其實,隨便把別人當(dāng)作“學(xué)院派”加以批判的人,不是以我劃線,就是以某一個與自己觀點相同的人劃線。同意的就是“現(xiàn)實派”,就是堂堂正正的學(xué)者;不同意者就是“學(xué)院派”,就是權(quán)貴的奴仆。這仍然是“文革”的遺風(fēng)。這不是說在學(xué)術(shù)批評中沒有是非,沒有對錯,沒有優(yōu)劣,沒有高下,而是說究竟誰對誰錯,誰是誰非,誰優(yōu)誰劣,誰高誰下,尚需要進一步討論。如果說在政治批判中是以成敗論英雄,那么,在學(xué)術(shù)沒有講述出山東周村在實行股份合作制中采取“分”與“賣”的方式量化存量資產(chǎn)的具體過程和完整故事,對問題的分析也比較簡單,不論是“分”與“賣”等價,還是“賣”優(yōu)于“分”,僅用兩個虛擬的數(shù)據(jù)是很難說明問題的。因此,作為項目負責(zé)人和主編,筆者認為,該文沒有達到天則所案例研究的要求,決定不收入《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第2集)(1999),同時取消資助。也許是筆者才疏學(xué)淺,缺乏政治敏感,至今仍未從中發(fā)現(xiàn)什么主張“賣”優(yōu)于“分”“就是為權(quán)貴私有化辯護”之類的含義。至于樊綱的《“不道德的”經(jīng)濟學(xué)》,筆者也有批評(張曙光,1999),認為道德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道德是非的理性判斷,二是道德實踐的價值判斷;作為理性判斷,道德是經(jīng)濟學(xué)的考察對象;作為價值判斷,道德純粹是每個人發(fā)自內(nèi)心的感受和選擇,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實踐,不是經(jīng)濟學(xué)討論的問題。樊綱沒有區(qū)分這兩個方面,把道德問題全部歸結(jié)為價值判斷問題,因而陷入了片面性。但是,認為經(jīng)濟學(xué)討論不討論道德問題與要不要和有沒有道德關(guān)懷是不同的兩回事。主張經(jīng)濟學(xué)不討論道德問題,是以道德作為前提包含其中的,不見得就是沒有和不要道德關(guān)懷;同樣,主張經(jīng)濟學(xué)要討論道德問題,也不一定就是堅持和充滿道德關(guān)懷。關(guān)鍵是討論什么,怎么討論?難道象傳統(tǒng)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xué)那樣,大講公有制經(jīng)濟中人與人的關(guān)系是同志式互助合作關(guān)系,每個人的行為都是一心為公,無私奉獻,就是堅持和充滿道德關(guān)懷嗎?難道經(jīng)濟學(xué)從經(jīng)濟人的角度,運用經(jīng)濟分析的方法(包括成本收益分析)來討論問題,而不從社會人、文化人、道德人的角度,運用非經(jīng)濟分析的方法來討論問題,就是不要和沒有道德關(guān)懷嗎?要求人們都從同一個角度,運用同一種方法,討論同一個問題,得出同樣的結(jié)論,豈不荒唐,那還要科學(xué)分工干什么?《樊文》是在學(xué)理的層面討論問題的,而《姚文》卻要將其推至政治的層面去批判。這就有點與風(fēng)車作戰(zhàn)的味道了。 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即任何一個學(xué)術(shù)概念或術(shù)語,比如“學(xué)院派”和“經(jīng)院哲學(xué)”,能不能轉(zhuǎn)義或重新定義?當(dāng)然可以。但是轉(zhuǎn)義和重新定義必須交待清楚,其價值和生命力取決于學(xué)界的認同和共識。如果把在大學(xué)和研究機構(gòu)中工作和討生活的學(xué)者看作是“學(xué)院派”,把在大眾傳媒部門工作的報刊學(xué)人看作“現(xiàn)實派”,那么,這就是以工作地點為標準來定義的。這兩類學(xué)人的知識背景、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觀察角度、議論風(fēng)格有很大的不同,對此作出分析和評論是有意義的。一般來說,前者提出和討論問題往往偏重于學(xué)理層面,后者往往偏重于現(xiàn)實層面;前者往往注重問題的歷史背景、前人的考察和現(xiàn)實的演變,后者往往注重于大眾的情緒和社會的反映,但是,這一定義既不是同一學(xué)科中不同學(xué)術(shù)流派的分野,更不包含“學(xué)院派”這一概念原來的政治含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dāng)前的中國不是“學(xué)院派”多了,而是“學(xué)院派”少了。滾滾商潮,已經(jīng)把“學(xué)院派”沖得個七零八落,很多人都變成了“現(xiàn)實派”,就是《姚文》作為“學(xué)院派”的代表加以批評的盛洪和樊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學(xué)院(派)味”不足,“現(xiàn)實(派)味”太濃了。 《姚文》一方面自稱外行,另一方面,又以外行人看不懂為由,猛烈抨擊“學(xué)院派”專門學(xué)者的風(fēng)范,是把更深奧、更富理論的純粹性,當(dāng)作是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xué)的特征。這就有點強辭奪理了。既然是專門理論,其讀者對象自然是專家學(xué)者,不是社會大眾,外行人就是看不懂。這是科學(xué)分工,非常正常,無可指責(zé)。如果外行人一看便知便懂,那還要專家學(xué)者干什么,難道學(xué)術(shù)論文和學(xué)術(shù)著作的價值要由外行人來評判,要以外行人能否看懂為標準嗎?作為一個經(jīng)濟學(xué)者,筆者最近讀福科的《知識考古學(xué)》,認真讀了一遍,有些地方還反復(fù)讀了幾遍,但很多地方還是沒有讀懂,難道能據(jù)以否定福科的價值嗎?既然自稱外行,那就應(yīng)當(dāng)先虛心學(xué)習(xí),而不是以一種權(quán)威的架式教訓(xùn)別人或?qū)e人打死。當(dāng)然,筆者既不贊同不費思索,把復(fù)雜問題簡單化,也不贊同故弄玄虛,把簡單的問題復(fù)雜化。 需要指出的是,將學(xué)理層面的問題扯到政治層面來討論,一個重要的結(jié)果是會產(chǎn)生一種轟動效應(yīng),甚至可以熱炒一陣,借以抬高身價,但是,對于科學(xué)的發(fā)展和理論的進步來說,這樣做能有多少助益?筆者實在是心存疑竇。可惜的是,我們的一些人熱衷此道,精于此道,因而,在現(xiàn)實中有兩大歪風(fēng)邪氣:一是抄風(fēng)甚烈,二是炒風(fēng)更盛。但是,此道乃仕途之道和商家之道,而非學(xué)問之道,真正的學(xué)者是不屑于這樣做的。只有那些半瓶子醋和心轅意馬的人,才視此為不二法門。筆者指出這一點,并不能使一些人不這樣做,只是希望大多數(shù)學(xué)者不要在這方面浪費時間。 3.真問題和假問題 在這場爭論中,秦暉先生提出了真問題和假問題、真學(xué)問和假學(xué)問的問題,并且認為何女士和《陷阱》講的是真問題,做的是真學(xué)問,而《分與賣》及其作者講的是假問題,做的是假學(xué)問。《姚文》也有此議論。這樣就在進行政治批判的同時,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哲學(xué)問題,也使這種政治批判具有了幾分哲學(xué)的色彩和依據(jù)。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問題,什么是假問題呢?它們是怎么提出來的? 真問題和假問題是30年代維也納學(xué)派提出的概念。目的在于反對黑格爾的形而上學(xué),其全部論點可以歸結(jié)為,形而上學(xué)的整個陳述都是假陳述。按照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在《通過語言的邏輯分析清除形而上學(xué)》一文中的分析和說明,假陳述有兩類:一類是包含一個被認為有意義的詞,但是,嚴格說來,在某一特定語言內(nèi),包含這個詞在內(nèi)的一串詞并不構(gòu)成一個陳述,因而是無意義的。這自然是一種假陳述。另一類是組成句子的詞是有意義的,因而在理論上可以分為有效的和無效的,真的和假的。如果這樣一串詞以一種違反句法的方式湊在一起,乍看起來貌似一個陳述,實際上并不構(gòu)成一個有意義的陳述,我們就稱它為假陳述。因此,假陳述就是貌似陳述而不是陳述,并不斷言任何東西,既不表現(xiàn)真命題,也不表現(xiàn)假命題,雖然它符合傳統(tǒng)語法的句法,但卻明顯地違背了邏輯的句法。可見,假陳述構(gòu)成的可能性在于語言的邏輯缺陷。由此看來,真陳述和假陳述、真問題和假問題一開始是從邏輯的意義上來講的。進一步才有經(jīng)驗陳述的真假問題。因為,一個有意義的陳述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第一類是有些陳述,其真實性只是由于它們的形式,如邏輯和數(shù)學(xué)的公式,它們本身并不是事實的陳述,只是用來使這種陳述變換形式。第二類是這些陳述的否定,它們自相矛盾,因而根據(jù)自身的形式便是假的。除此而外的其他陳述,其真假的判定在于記錄的句子,它們是經(jīng)驗陳述,屬于經(jīng)驗科學(xué)的范圍。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所謂真陳述和假陳述、真問題和假問題有兩種,一種是邏輯陳述或邏輯問題的真假,一種是經(jīng)驗陳述或經(jīng)驗問題的真假。《秦文》并沒有說明他是在何種意義上來討論真假問題的,而且從整個文章來看,在一定程度上混淆這兩種問題,不過從其內(nèi)容來看,他是在經(jīng)驗陳述的意義上來講的,討論的是現(xiàn)實中的真問題和假問題,既沒有涉及邏輯陳述的真假,也沒有涉及邏輯陳述和經(jīng)驗陳述及其真假之間的關(guān)系。其實,經(jīng)驗陳述的真假是一個實然的問題,而邏輯陳述的真假是一個應(yīng)然和非實然的問題。理論的創(chuàng)造和學(xué)術(shù)的生產(chǎn)有其自身的邏輯,理論上和邏輯上的真問題不見得就是現(xiàn)實中和經(jīng)驗上的真問題;反過來,現(xiàn)實中的真問題也未必是理論上的真問題,根據(jù)理論邏輯所作的討論,其直接目的不是站在當(dāng)事人的立場上去解決什么現(xiàn)實問題,而是站在學(xué)者的立場上和文化發(fā)展的立場上,做知識增量的添加和積累。不僅如此,現(xiàn)實中的任何一個問題都是被理論和邏輯建構(gòu)的。例如,貧困問題,如果不能在理論上定義出貧困線,那么,我們是無法提出和討論貧困問題的。因此,關(guān)鍵是所論問題是從什么邏輯上提出和解決的。弄清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對《秦文》的討論作出進一步的評論。 應(yīng)當(dāng)肯定,《陷阱》提出和討論的問題是現(xiàn)實中的真問題,這正是它的價值所在。在這一點上,《秦文》是正確的。但是,有了真問題,是不是就有了真學(xué)問?筆者認為不一定。一方面,這要看你是從什么邏輯上提出和解決的,另一方面,還要看你的理論邏輯能否貫徹到底。就此而論,《陷阱》是有缺憾的,其表現(xiàn)之一就是,《陷阱》雖然提出和討論了一些重大而尖銳的現(xiàn)實問題,但是,我們既看不到它的歷史演變,也看不到它的未來發(fā)展,其理論框架和理論模型的邏輯連貫性、系統(tǒng)性和經(jīng)驗可證偽性,更是無從談起;其表現(xiàn)之二是(舉個例子),從否定股份制改造對轉(zhuǎn)換經(jīng)營機制的動機和作用,到肯定對重組國有資產(chǎn)的目的和作用。 《秦文》對《陷阱》的肯定是對的,但對《“分”與“賣”》的否定卻是錯誤的。“分”與“賣”也是現(xiàn)實中的真問題。在實行股份合作制的過程中,究竟是采取分配的方式,還是采取售賣的方式,以及形成怎樣的產(chǎn)權(quán)結(jié)構(gòu),是人們在改革實踐中提出和探索的問題,凡是稍有經(jīng)驗的學(xué)者,誰也不會否定這一問題在現(xiàn)實中的客觀存在。既然如此,經(jīng)濟學(xué)家為什么不能提出和討論這樣的問題,提出和討論這樣的問題怎么就成了假問題呢?我們不知道《秦文》究竟根據(jù)什么邏輯作出這樣的判斷?既然有“分”和“賣”兩種方式,自然就提出了二者是等價的還是有優(yōu)劣之別的問題,在怎樣的條件下等價和在怎樣的條件下“賣”優(yōu)于“分”或“分”優(yōu)于“賣”的問題,以及為什么一些地方和一些方面選擇了“分”,而另一些地方和另一些方面選擇了“賣”的問題,這都是值得探索的重要的現(xiàn)實問題。我們也不知道《秦文》根據(jù)什么邏輯認為“分”就是“民主私有化”,就值得提倡,而“賣”就是“權(quán)貴私有化”,就需要反對?須知,我國目前的公有制經(jīng)濟(包括國有經(jīng)濟和集體經(jīng)濟)是通過政府的強制性安排建立起來的,在其建立之時,并沒有形成一套初始的合約;當(dāng)我們燒毀了地契,取消了定息,也就摧毀和消滅了契約關(guān)系。今天的市場化改革,說到底就是要重新訂立契約和契約關(guān)系,其具體途徑就是“分”和“賣”,至于在何種情況下“分”,在何種情況下“賣”,這是當(dāng)事人的選擇,與什么民主私有化和權(quán)貴私有化粘得上嗎? “假作真時真亦假”。需要指出的是,既然“分”與“賣”的問題是現(xiàn)實的真問題,那么,把真問題說成是假問題的問題,自然就是假問題了。這與《秦文》關(guān)于“姓資”“姓社”的問題是假問題的判斷,所依據(jù)的是同一個邏輯。標榜自己是真問題,借以否定別人的真問題,把對手置于一個荒誕的地位上,然后加以討伐。這是《秦文》、《姚文》和《陷阱》的一個共同手法。 需要指出的是,《“分”與“賣”》從現(xiàn)實中提出問題,然后在經(jīng)濟學(xué)的邏輯框架內(nèi)加以討論,在理論的發(fā)展和知識的積累上也是有意義的,是邏輯上的真問題。不足之處是,這方面的功夫下得不夠,帶來的知識增量有限。 4.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 以上兩節(jié)的討論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即學(xué)者之間的交往應(yīng)當(dāng)采取一個什么態(tài)度,具備怎樣的精神?才能建立正常的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形成良好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氣,進而推動學(xué)術(shù)的繁榮和發(fā)展。這就是筆者前述答問的中心思想。 在學(xué)術(shù)思想的發(fā)展中,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自由主義和功利主義存在著嚴重的對立和不斷的沖突。如果說,在學(xué)術(shù)思想的領(lǐng)域內(nèi),這種對立和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激勵學(xué)者們進行研究和探索的話,那么,當(dāng)其與某種外在的需求,特別是政治的需要和政治的變故聯(lián)系在一起時,就會阻礙學(xué)術(shù)的進步和理論的發(fā)展。于是,在當(dāng)代的學(xué)術(shù)發(fā)展中,很多人致力于探討擺脫困境的途徑。在這里,哈貝瑪斯提出的“交往理性”(1994),也許可以成為處理學(xué)者之間相互爭論的倫理原則。據(jù)筆者的理解,堅持“交往理性”的原則,并不是要學(xué)者放棄自己的選擇自由和理論立場,而是要學(xué)者在相互交往時能夠彼此尊重,寬厚禮讓,避免誤解、曲解,從而達成“同情的理解”和某種真正的“共識”;或者如布迪厄所說,學(xué)者們在各自場域的競爭中,不是試圖去壓倒對方,而是著眼于彼此的理解和創(chuàng)新。為此,就需要探索和營造達成“理解”和“共識”的社會條件。 從“交往理性”的思想出發(fā),對于前面的討論以及我們這里提出的問題,人們會有一些新的認識。 第一,社會是多元的,思想和主義也是多元的。這是“交往理性”賴以建立和實施的基礎(chǔ)和前提。企圖只允許一種思想、一種主義,禁止別的思想和別的主義,不僅是辦不到的,而且是在扼殺學(xué)術(shù)。這一點,國內(nèi)學(xué)人都有切膚之痛,我相信大家都會記憶猶新。《陷阱》揭示了當(dāng)代中國的一系列現(xiàn)實矛盾和現(xiàn)實問題,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和共鳴,是社會所需要的,自然有其價值。對此應(yīng)當(dāng)承認和肯定,并作出恰當(dāng)?shù)脑u價。但是,中國之大,人口之多,社會之復(fù)雜,加之處于巨大變革之中,僅有《陷阱》一類作品也是不夠的和不行的,既不可能對中國的現(xiàn)實作出全面的描述和刻畫,也不可能對中國的問題作出多方面、多角度的剖析和解釋,更不可能滿足如此廣泛、復(fù)雜的社會需求。“學(xué)院派”的作品也是需要的,也是有價值的,也應(yīng)當(dāng)承認和肯定,并作出恰當(dāng)評價。以此之價值否定彼之價值是不適當(dāng)?shù)模瑧岩梢磺校穸ㄒ磺校虻挂磺校Y(jié)果連自己也否定了。這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說,面向社會的暴露和吶喊需要,訴諸理性的沉思和邏輯的分析也需要;形而下的東西需要,形而上的東西也需要;面向廣大受眾的報刊作品需要,面向少數(shù)專家學(xué)者的作品也需要;直接取自現(xiàn)實、針對現(xiàn)實的作品需要,從前人研究中發(fā)現(xiàn)和提出問題,以及考據(jù)索證的作品也需要。試想想,如果我們的社會中只有《陷阱》一類作品,那會是一種什么樣子呢?就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樣,大家只能看樣板戲,唱語錄歌,跳忠字舞,那還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和正常的生活嗎?簡直是不堪回首! 第二,社會科學(xué)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社會科學(xué)研究實踐應(yīng)當(dāng)充分體現(xiàn)出獨立性和自主性。這也是建立和實施“交往理性”的重要前提。對于社會科學(xué)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鄧正來先生借助布迪厄的理論作過認真的討論(1996)。對此,國內(nèi)學(xué)界關(guān)注和理解得不夠。社會科學(xué)的這種特性要求,它應(yīng)當(dāng)獨立地自主地確立自己的社會需求和社會作用,不應(yīng)當(dāng)迎合社會讓它充當(dāng)合法化或社會操縱工具的要求,社會科學(xué)家也不能依靠其他力量來確立自身的地位,只能借助于自己研究的邏輯。為此,社會科學(xué)研究首先應(yīng)當(dāng)建構(gòu)自己的研究對象,而不是隨意地簡單地將那些對社會、政治、經(jīng)濟具有重大意義的經(jīng)驗現(xiàn)象作為研究對象,如果能夠把社會上不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建構(gòu)成科學(xué)對象,或者能夠從一個意想不到的新視角重新審視某個在社會上備受矚目的話題,那么,其力量就會突顯出來。其次應(yīng)當(dāng)對抗和清除知識界內(nèi)部的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一方面要減少和消除因互相吹捧和彼此支配而產(chǎn)生的大量毫無學(xué)術(shù)意義的論題,另一方面要減少和清除那些煽起毫無學(xué)術(shù)價值的爭辯和毫無學(xué)術(shù)建樹的提升。然而,《陷阱》及其擁護者卻對此持否定態(tài)度。他們認為,社會科學(xué)不需要建構(gòu)自己的研究對象,只要把那些有重大意義的經(jīng)驗現(xiàn)象作為研究對象,就會有真問題和真學(xué)問,誰要是不這樣做,或者不贊同這樣做,那么,他們搞的就是假問題和假學(xué)問,是“淮桔成枳” ,是“屠龍術(shù)”的表演。并借此引起一些沒有什么學(xué)術(shù)價值的爭論,甚至冷嘲熱諷,喜笑怒罵。筆者真不明白,這種作法對于確立社會科學(xué)的自主性能夠有多大幫助。這里,筆者想討論一下《陷阱》及其擁護者挑起和進行爭論一種方法,即“化約論”方法。 任何一個理論都不是無限定的,而是有限定的,因而,不能作簡單的化約。比如,在當(dāng)代的中國,凡討論市場經(jīng)濟的學(xué)者,都承認市場的缺陷,沒有人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只是在對市場作用的大小、方面、方式等方面存在分歧。這很正常。同樣,凡討論產(chǎn)權(quán)的學(xué)者,也沒有人認為私有制美好無比,威力無邊,都承認在現(xiàn)代社會,私有產(chǎn)權(quán)和公有產(chǎn)權(quán)各有其地位和作用,只是偏于前者或偏于后者的權(quán)重不同而已。與此密切相關(guān),提出保護私有產(chǎn)權(quán),自然是保護誠實勞動和正當(dāng)交易獲得的財產(chǎn),而不保護靠權(quán)錢交易、貪污腐敗和化公為私得到的非法財產(chǎn),這種限定不言自明,似乎是一種常識。雖然后者在現(xiàn)實中大量存在,且二者之間的界限有些也很難分得十分清楚,但在理論上的限定還是清楚的。然而,《陷阱》作者及其擁護者卻不這樣看,他們拋開理論上的限定,作了一種化約論式的處理,然后加以批判。你講市場經(jīng)濟,他就說是“市場萬能”;你講私有產(chǎn)權(quán),他就認為是“私有制萬歲”;你講保護私有產(chǎn)權(quán),他就說是化公為私“合理論”。退一步講,即使講了市場和私有制的巨大作用,講了化公為私合理之類的話,也有個在怎樣的語境中講的問題。難道可以不問具體環(huán)境條件和語境,簡單加以化約嗎。筆者在評論《中國人的道德前景》(茅于軾,1998)時,贊賞了茅于軾教授關(guān)于“私有制不僅不是萬惡之源,而且是“道德之神””論斷,但茅教授的討論是有限定的。他認為,有了私有制,才產(chǎn)生了交換,才有了商業(yè)社會,才造成了今天豐富的物質(zhì)生活,因而,凡是能夠促進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都是符合道德的。筆者明確指出,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再以權(quán)錢交易、化公為私而論,它的產(chǎn)生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計劃制度和市場制度的共時存在,這種現(xiàn)象的確相當(dāng)普遍,必須堅決反對,但決不能說所有發(fā)了財?shù)娜硕际菣?quán)錢交易,都是化公為私。因此,化約論的處理不僅在理論上是不恰當(dāng)?shù)模鼤鸷芏嗪翢o學(xué)術(shù)價值的爭論,破壞學(xué)者之間的理性交往,而且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它會使我們的政策操作走到邪路上去。同樣,筆者也不同意某些人隨意給別人扣上什么新“左派”的帽子。這些都非嚴肅學(xué)者之所為。在學(xué)者中,學(xué)術(shù)流派是需要的,政治上的劃派是不需要的。用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分野替代學(xué)術(shù)上的討論,是學(xué)界和學(xué)人的悲哀。 第三,學(xué)者是自由人,寫不寫,說不說,寫什么,說什么,怎么寫,怎么說,都由其作出選擇,并為自己的決策負責(zé)。別人無權(quán)指手劃腳,強迫學(xué)者這么辦,那么做。如果按照別人的旨意去寫去說,那就不是學(xué)者,而是御用文人。這也是堅持“交往理性”必須具有的信念和遵循的行為準則。過去,在傳統(tǒng)體制的集中控制之下,學(xué)者沒有創(chuàng)作的自由,往往被迫就某些事情表態(tài)。因而釀成了很多學(xué)者的悲劇。改革開放20年來,這方面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進步,學(xué)者的自由度比過去大多了,如有不同意見,至少可以保持沉默,沒有人逼著你去講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了。但是,還遠遠不夠。一方面,有些敏感的話題不能講,有些理論的禁區(qū)不能討論,有些政策不能批評。講了有人就會興師問罪。另一方面,一些學(xué)者的參與意識很強,總想使自己的主張為決策者采納,并且以采納的情況作為評判的標準。這樣,也就喪失了學(xué)者的獨立性。其實,只要給學(xué)者以講話的自由,給決策者以選擇的自由就可以了。你可以講,可以批評,我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因此,保持一定的距離和一個超然的態(tài)度也許更符合學(xué)者的地位和身份。然而,《姚文》不僅沒有推動這方面的進步,反而有點向后退的味道。作者一方面對《陷阱》關(guān)于“整個中國當(dāng)代經(jīng)濟學(xué)的活動,基本上是一種“屠龍術(shù)”的表演”的批評大加贊嘗,另一方面,對“學(xué)院派”的淡漠又耿耿于懷,批評盛洪關(guān)于“過渡經(jīng)濟學(xué)派”的介紹,“對何清漣的轉(zhuǎn)軌經(jīng)濟學(xué)不置一詞”,經(jīng)濟學(xué)界的“圈內(nèi)人士”流傳著“對《現(xiàn)代化的陷阱》的非學(xué)術(shù)純粹性的不屑的傳聞”等等,這就給人一個強烈的印象,經(jīng)濟學(xué)界想用沉默和流言蜚語來封殺《陷阱》。因而,其無言的結(jié)論是:沉默就是怯懦,就是罪過。這不是筆者的推論,而是《姚文》對“學(xué)院派”喜笑怒罵流露出來的真實含義。 第四,學(xué)者要有自知之明,既不可對自己估計過高,又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局限。這也許是堅持“交往理性”最難做到的事情,也是很多學(xué)人(包括本人)的通病。在《姚文》點名批評的人中,有人也有這樣的毛病。比如,作為經(jīng)濟學(xué)家,當(dāng)然可以對其他領(lǐng)域的問題發(fā)表自己的看法,就象秦暉和自稱外行的姚先生對經(jīng)濟學(xué)和經(jīng)濟學(xué)家那樣,但是,頭腦必須清醒,相對于其他領(lǐng)域的專家,自己的知識積累和文獻涉獵明顯不足,因而就更要謹慎,更要謙虛。然而,有人恰恰犯忌。《陷阱》的作者及其擁護者也犯有同樣的毛病。 《陷阱》是一本什么樣的著作?筆者認為,是一本大眾讀物,而不是學(xué)術(shù)著作。從大眾讀物來看,作者針對當(dāng)前時弊和大家關(guān)注的問題,搜集了大量報刊資料,加以系統(tǒng)的歸納,再加上比較流暢的文筆,的確是一本不錯的東西。這也是該書暢銷的一個原因。但是作為學(xué)術(shù)著作,嚴格來說,不要說不夠格,可以說還沒有入門。這也許是學(xué)界(包括經(jīng)濟學(xué)界和其他學(xué)界)不愿理采的原因,筆者開始不想涉及就是這樣。社會學(xué)界的一朋友告訴我,他在風(fēng)入松討論會上對《陷阱》提出類似的批評,竟被何女士譏之為,“某某某根本沒有讀懂我的書”。這里,筆者想講一個真實的故事。近20年來,以趙人偉教授為首,包括李實、朱玲、張平等研究員在內(nèi)的收入分配課題組,作了大量的調(diào)查研究,出版了一部專著(1994)和發(fā)表了大量文章,第二部專著正在出版之中,被國內(nèi)外經(jīng)濟學(xué)界公認為是目前研究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最高水平之一。去年,李實教授在香港作有關(guān)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學(xué)術(shù)報告,何女士當(dāng)眾評論是,你們這一套根本沒有用,只有她在《陷阱》中講的才是有意義的。說實在的,這未免有點太自負了。關(guān)于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陷阱》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人民大學(xué)根據(jù)他們于1994年在全國范圍內(nèi)作的一次嚴格PPS抽樣入戶調(diào)查問卷的數(shù)據(jù)所作的計算,我國城鄉(xiāng)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shù)為0.434,同年,按家庭戶收入分組計算的基尼系數(shù)為0.445,這已經(jīng)超過了西方國家通常的基尼系數(shù)”(第235頁)。首先,這一引文沒有出處,使他人無法檢索和查找,這就不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這種情況在《陷阱》中并不少見,而且有一個明顯特征,凡引自報刊上的一般文章,大都注有出處;但引自學(xué)術(shù)論著的,大都沒有出處。筆者實在不懂得這是為什么?似乎只能有一個解釋,既要引用“學(xué)院派”的東西,又要與“學(xué)院派”劃清界限。經(jīng)筆者與有關(guān)作者和出版者查對,這里的資料系引自李強、洪大用、宋時歌的論文《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異分析》,發(fā)表在《中國科技導(dǎo)報》1995年第11期上。其次,這兩個數(shù)據(jù)是有錯誤的。從目前的發(fā)展來看,計算基尼系數(shù)有三種方法:一是按家庭總收入計算,二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家庭為單位計算,三是按家庭人均收入但以個人為單位加權(quán)計算。由于每戶平均人口數(shù)隨收入提高而減少,1994年,最低收入戶和低收入戶分別為3.72人和3.57人,而高收入戶和最高收入戶分別為3.01人和2.81人,所以按家庭戶收入計算的基尼系數(shù)必然小于按家庭人均收入計算的基尼系數(shù);以家庭為單位計算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數(shù)也小于以個人為單位加權(quán)計算的人均收入基尼系數(shù)。為了驗證這一結(jié)論,李實教授利用他們課題組1995年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專門上機進行了計算,按上述三種方法計算的結(jié)果依次是0.409,0.444和0.445。筆者以為,從計量方法來看,搞計量分析的經(jīng)濟學(xué)家自然要比社會學(xué)家精通。因此,這里主要責(zé)任在原文作者,《陷阱》只是引用,但以經(jīng)濟學(xué)家自稱的何女士,居然沒有發(fā)現(xiàn)這里的錯誤,可見其對基尼系數(shù)的理論和方法也不甚了了。再次,象李實教授這樣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xué)的理論功底非常扎實,經(jīng)濟計量分析方法又相當(dāng)熟練的經(jīng)濟學(xué)家在國內(nèi)的確不多,且又長期從事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與之合作的國內(nèi)外專家學(xué)者,都對其研究和著述的水平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但在何女士的眼里卻是一堆垃圾,糞土不如。寫到這里,象何女士這樣狂妄、自負、自不量力之人,筆者實在少見。 應(yīng)當(dāng)指出,《陷阱》的基本寫法是,列舉一大堆資料和案例,然后下一個簡單的概括性斷語,再加以情緒化的宣染,僅此而已。其所使用的概念不是學(xué)術(shù)概念,如什么“光環(huán)市場”和“環(huán)上市場”及其所作的簡單運算(第65頁);其分析也不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在學(xué)術(shù)上沒有什么前進,沒有什么深度,也沒有提供多少新的信息量。就是其從報刊上引用和自己計算的數(shù)據(jù),也有很多是錯誤的,只要覺得它合自己的口味,而根本沒有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實際。例如,“1992年香港資本市場總量的十分之一均投向大陸房地產(chǎn)業(yè)”(第51頁)。“據(jù)估計,中國這幾年開放房地產(chǎn)市場所吸納的外資,占了“引進外資”總額的90%左右”(第52頁)。作者注明,前一個數(shù)據(jù)引自《中外房地產(chǎn)導(dǎo)報》(1993年第6期),后一個引自香港《當(dāng)代》月刊(1993年9月號),但這兩個數(shù)據(jù)都是錯誤的。須知,香港資本市場總量和大陸在香港資本市場籌資總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果是指大陸在香港資本市場籌資總量的十分之一,也許還差不多,但要說是香港資本市場總量的十分之一,則肯定有誤;至于引進外資中90%投入房地產(chǎn)云云,更是沒有譜的事情了。這里,筆者根據(jù)《中國統(tǒng)計年鑒》及有關(guān)文獻提供幾個數(shù)據(jù),讀者自己去判斷。1992和199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chǎn)投資中,引進外資分別為457.14億元和907.29億元,占5.8%和7.3%;1993年在全部基本建設(shè)投資中,用于房地產(chǎn)的投資為140.9億元,占全部基建投資的3.1%;即使全部房地產(chǎn)投資都是外資,也只占引進外資的15.5%。另據(jù)外經(jīng)貿(mào)部提供的資料,從1979-1996年,在利用外資中,房地產(chǎn)和公用服務(wù)業(yè)項目24801項,占10.1%,協(xié)議利用外資1268.64億元,占27.3%(王洛林,1998)。從《陷阱》一書對數(shù)據(jù)的使用中,人們不難看到,何女士還缺乏對中國經(jīng)濟運行的基本感覺和基本把握,否則,不會鬧這樣的笑話。再如,“到1996年底,我國商品房積壓已超過6800萬平方米,由此發(fā)生的資金沉淀達1200萬億元”(第62頁)。按此計算,1 平方米住房的價格是1750萬元。筆者真不懂這樣的帳是如何算的。也許作者會說這是筆誤或者印刷錯誤。但這樣的錯誤對于嚴肅的學(xué)術(shù)著作是不能容許的。 如果說,作為記者,何女士對中國經(jīng)濟運行實際缺乏起碼的感覺和認識還有情可原,那么,對于文獻的隨意曲解和運用就是不能容忍的了。為了顯示自己的博學(xué),何女士在《陷阱》中引用了很多文獻,在發(fā)表的文章中也是如此,但在很多地方是曲解的,與文獻的原意是相反的。這里僅舉一例。在《陷阱》中有這樣一段話,這段話也出現(xiàn)在何女士發(fā)表在《天涯》雜志的文章中,現(xiàn)抄錄如下。“公平與效率,在經(jīng)濟學(xué)、哲學(xué)等一切社會科學(xué)和人文科學(xué)領(lǐng)域,都是一個帶有終極意義的基本命題。它的意義,不僅僅只在于它能否為地球村的全體居民在現(xiàn)實中尋求到公平和正義,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為一種理想,植根于社會制度和人們心中,成為人們世世代代追尋的目標。可以說,本世紀共產(chǎn)主義運動就是人類尋求公平的大規(guī)模的實踐。我們從巴貝夫的《平等共和國》、圣西門的《實業(yè)制度》、傅立葉的《和諧制度》這些19世紀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本世紀不少杰出學(xué)者的著作,如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岡納.繆爾達爾的《世界貧困的挑戰(zhàn)》《亞洲的戲劇》等,都能清晰地看到他們對“社會公正”這一人類理想的張揚和追求”(第358頁)。大家知道,哈耶克和繆爾達爾同是1974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xué)獎獲得者,但兩人的觀點卻完全不同。在哈耶克的著作中,“社會公正”是有明確定義的,而且哈氏對此持堅決的批判立場。他在討論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問題時明確指出,“為救濟貧困而設(shè)計的制度性安排已經(jīng)逐漸變成了一種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的手段:這種再分配在表面上所依據(jù)的乃是某些人認為的社會正義原則(現(xiàn)實中并不存在這種社會正義原則),然而在實質(zhì)上卻是由特定的決策所決定的”。“在一個社會將消滅貧困和保障最低限度的福利視作自身職責(zé)的事態(tài),與一個社會認為自己有權(quán)確定每個人之“公正”地位并向其分配它所認定的個人應(yīng)得之物的事態(tài)之間,實存在著天壤之別。當(dāng)政府被授予提供某些服務(wù)的排他性權(quán)力的時候,自由就會受到極為嚴重的威脅,因為政府為了實現(xiàn)其設(shè)定的目標,必定會運用這種權(quán)力對個人施以強制”(1960)。所以,在哈耶克看來,所謂“社會公正”就是“公正的分配”,它是福利國家“追求傳統(tǒng)社會主義目標的新方法”,是對自由的嚴重威脅,是通向奴役的道路。然而,在何女士的筆下,哈耶克竟成了“社會公正”的代言人和衛(wèi)道士。這里,筆者既無意懷疑何女士張揚和追求公正和正義的立場,也無意贊同哈耶克的觀點,而是想指出,何女士是采用什么戲法把哈耶克從“社會公正”的“死敵”變成了它的擁護者?哈耶克如果地下有知,不知該作何感想?因此,筆者實在納悶,何女士是否真的讀過她提到的這些著作,并讀懂了這些著作? 問題的要害并不在這里。如果作者能真正象后記中講的那樣,《陷阱》“不是為圈內(nèi)人寫的”,也不必這樣較真,但是,作者卻偏偏要把它說成是學(xué)術(shù)著作,而且是學(xué)術(shù)水平很高的著作。去年4月11日,《深圳商報》發(fā)表了記者采訪何女士的長篇報導(dǎo)(整整一大版;陳實,1998),何女士說,人們都說深圳是文化沙漠,聽說《北京青年報》等兩家報紙最近發(fā)表文章說,北京、上海學(xué)術(shù)研究的總體水平高于深圳,但近10年來,在全國有大震撼力的著作都是廣東學(xué)者寫的,如《山坳上的中國》、《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現(xiàn)代化的陷阱》三本著作,以及林賢治寫的長達5萬字的長文《胡風(fēng)事件:20世紀最大的精神事件和政治事件》。以筆者愚見,嚴格說來,三本書都不是學(xué)術(shù)著作。第一本書的作者對其定位很明確,大眾讀物,第二本是一個傳記,第三本也是大眾讀物。第一本書和林賢治先生的長文筆者沒有閱讀,不敢妄評;比較而言,第二本書的水平高于第三本,作者至少給我們提供了有關(guān)陳寅恪很多顯為人知的資料,也有不少對傳主思想的精彩分析,筆者讀完該書,對其中描述陳寅恪“獨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文字印象極深,但該書的最大缺陷是,作者對自己的對象采取了一種仰視的態(tài)度,對其局限基本未予涉及。這是傳記的最大忌諱。至于《陷阱》, 不僅作者本人說它是學(xué)術(shù)著作,甚至主編還要加上一句,說它比學(xué)術(shù)“更學(xué)術(shù)”(第393頁)。既然如此,筆者還能說什么呢。如果中國的學(xué)術(shù)是這個樣子,那么,這是中國學(xué)者的悲哀。如果這就是中國經(jīng)濟學(xué)的最高成就,那么,中國的經(jīng)濟學(xué)研究就仍然處在改革以前的年代。 不僅如此,為了抬高自己,作者及其擁護者對整個經(jīng)濟學(xué)界大加貶斥,如認為“整個中國當(dāng)代經(jīng)濟學(xué)的活動,基本上是一種“屠龍術(shù)”的表演”。“在長達數(shù)年的理論準備中,經(jīng)濟學(xué)家中很少有人去正視這一現(xiàn)實”(指股份制改造中的扭曲現(xiàn)象),因而造成“經(jīng)濟學(xué)家的悲哀:淮桔成枳”(第21-22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jīng)濟學(xué)家有了不少進步,在改革開放中也作出了一些貢獻,當(dāng)然,中國經(jīng)濟學(xué)家的整體水平還不高,在探索中也有這樣那樣的錯誤,經(jīng)濟學(xué)家應(yīng)當(dāng)接受各方面的批評,筆者不同意對中國經(jīng)濟學(xué)的進步和經(jīng)濟學(xué)家的貢獻作過高的評價。在當(dāng)代的中國,經(jīng)濟學(xué)貴為顯學(xué),但卻潛藏著很大的危機;經(jīng)濟學(xué)家雖是時代的寵兒,但卻有被寵壞的危險,有人也許被寵壞了;經(jīng)濟學(xué)家應(yīng)當(dāng)謙虛謹慎,不應(yīng)當(dāng)以“經(jīng)濟學(xué)帝國主義”的態(tài)度行為;經(jīng)濟學(xué)家應(yīng)當(dāng)象布迪厄反思社會學(xué)那樣(1998),認真反思,即對經(jīng)濟學(xué)理論和經(jīng)濟學(xué)家的學(xué)術(shù)實踐進行反思。在理論反思中,既要對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xué)以及立足于此的社會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xué)進行反思,也要對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xué)進行反思,還要對中國古代的經(jīng)濟思想進行梳理和闡釋,以便解決經(jīng)濟學(xué)的本土化問題,建立和發(fā)展中國的經(jīng)濟學(xué),對中國的經(jīng)濟運行和發(fā)展作出自己的解釋。在經(jīng)濟學(xué)家學(xué)術(shù)實踐的反思方面,既要對經(jīng)濟學(xué)家的生存條件和社會狀況有一個恰當(dāng)而清醒的認識,又要對經(jīng)濟學(xué)的科學(xué)場域進行反思,還要對經(jīng)濟學(xué)家的科學(xué)慣習(xí)作出反思,只有這樣,經(jīng)濟學(xué)家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行動自由。然而,筆者不明白,整個中國經(jīng)濟學(xué)界都是一些“淮桔成枳”的低能兒,是一些只會作“屠龍術(shù)”表演的冒牌貨,只有《陷阱》的作者鶴立雞群,獨具慧眼,那么,我們?nèi)绾谓忉屩袊?jīng)濟學(xué)研究20年來的進步,如何解釋中國經(jīng)濟學(xué)家在改革開放中作出的貢獻。既然如此,《陷阱》完全可以獨樹一幟,為什么要擠進“過渡經(jīng)濟學(xué)派”的行列,為什么要這些“低能兒”和“冒牌貨”去賞識呢。老實說,《陷阱》本身在邏輯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又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但愿我們大家都能記住先哲們的至理名言,并且下功夫去實踐。 第五,學(xué)者要有獨立的人格,在相互的交往中,要實而不虛,卑而不亢,要恪守兩條基本規(guī)則:一是對親近者要少一點吹捧,多一點批評,對疏遠者要多一些尊重,少一點輕視。這也是實踐“交往理性”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真正作到這一點并不容易,特別是在世俗化泛濫和市儈哲學(xué)流行的情況下,一些人恰恰相背而行。這一點在書評類文章中體現(xiàn)得最為清楚。這里有幾種情況,一是互相捧場,這一點我們在《陷阱》作者與其擁護者互相褒揚的文字(何清漣,1998)中已經(jīng)看到了。其實,按照一些人的水平,不至于看不到其中的問題,但只要陷入這個怪圈之中,往往難以自拔。二是有礙于情面,朋友、同事、師生,因而不得不說一些捧場的話,但要注意,千萬不要言過其實,該批評的還要批評,不過,遣詞用語需要斟酌。筆者在評論幾位學(xué)界同仁的著作時,曾經(jīng)有意地加強了批評的力度,所得效果不錯,有的關(guān)系甚至比以前更好。因此,我覺得,學(xué)界有德性、有教養(yǎng)者大有人在,大可不必把那些庸俗的東西帶到這方凈土中來。 5.小結(jié) 從以上的評論以及現(xiàn)實的狀況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雖然不是人人如此,但也有著相當(dāng)大的概率。即,原來處于正統(tǒng)地位的人很多變成了現(xiàn)行社會和市場制度的批判者,而原來被排除在正統(tǒng)思想之外的人,很多又成了擁護者;經(jīng)濟學(xué)家中的很大一部分成為了改良主義者,對一些通過漸進的、過渡的和贖買的辦法推進了市場化的改革多有贊揚,而政治學(xué)者、社會學(xué)者中的很大一部分,則采取了比較激進的立場。這種情況并非偶然,也值得思考。筆者不想對其作出象樣的解釋,事實上也勝任不了。只是想指出一點,即經(jīng)濟學(xué)家的職業(yè)習(xí)慣使其將效率判斷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在經(jīng)濟學(xué)的研究中,事實判斷除了包含有關(guān)經(jīng)濟過程的一般事實和論斷外,集中表現(xiàn)為效率判斷。不僅如此,價值判斷也不能從事實判斷中推導(dǎo)出來。例如,財富分配本身并不包含它是否公正的信息,即事實在邏輯上并不包含它的評價,公正與否的評價是判斷者主觀加上去的。這是由于價值判斷所依據(jù)的是道德標準,而事實判斷所依據(jù)的是一個與道德原則不同的標準和規(guī)范。當(dāng)然,價值標準可以通過實證研究和事實判斷來說明其正確與否,在經(jīng)濟研究中還要進行效率再判斷。這就要看它能否推動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人類的進步。筆者在本文結(jié)語中寫下這樣的內(nèi)容,目的在于希望不同學(xué)界的學(xué)者加強交流,經(jīng)常溝通,達成更多的理解和真正的共識。 參考文獻: 1. 何清漣,《經(jīng)濟學(xué)理論和“屠龍術(shù)”》,《讀書》,1997年第3期。 2. 樊綱,《“不道德的”經(jīng)濟學(xué)》,《讀書》,1998年第6期。 3. 姚新勇,《“不道德”的經(jīng)濟學(xué)的道德誤區(qū)》,《讀書》,1998年第11期。 4. 秦暉,《有了真問題才有真學(xué)問》,《讀書》,1998年第6期。 5. 盛洪,《論社區(qū)資產(chǎn)個人化的途徑:“分”與“賣”——以周村為典范的股份合作化過程為例》,《管理世界》,1998年第3期。 6. 張曙光(執(zhí)行主編),《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第2集),中國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1999。 7. 張曙光,《經(jīng)濟學(xué)家如何講道德——評〈中國人的道德前景〉》,《讀書》,1999年第1期。 8. 茅于軾,《中國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學(xué)出版社,1998。 9. 卡爾納普,《通過語言的邏輯分析清除形而上學(xué)》,載洪謙主編,《邏輯經(jīng)驗主義》(上),商務(wù)印書館,1982。 10. 哈貝瑪斯,《交往行動理論》(兩卷),洪佩玉等譯,重慶出版社,1994。 11. 鄧正來,《關(guān)于中國社會科學(xué)自主性的思考》,《中國社會科學(xué)季刊》,1996年11 月冬季卷(總第17期)。 12. 韓毓海,《相約98,告別98——新年答客問》,《中國圖書商報》,1999年2 月9日。 13. 趙人偉,基斯·格里芬(主編),《中國居民收入分配》,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4。 14. 李強、洪大用、宋時歌,《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異分析》,《中國科技導(dǎo)報》,1995年第11期。 15. 王洛林(主編),《中國外商投資報告》,經(jīng)濟管理出版社,1998。 16. 陳實,《何清漣:冷眼旁觀“陷阱”熱》,《深圳商報》,1998年4月11日。 17.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譯本),鄧正來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 18.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5。 19. 布迪厄,《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xué)導(dǎo)引》。 20. 老子,《上篇道經(jīng)三十三章》,《下篇道經(jīng)八十一章》。 21. 何清漣,《必須從0比0 開始——讀秦暉〈天平集〉》,《半月讀書》,1998年 第1期. 1999/2/5初稿 1999/3/10修改,于北京三里河 本文構(gòu)思過程中,曾與汪丁丁、王焱交換過意見,初稿請陳家映、徐友漁、鄭也夫、黃平、石小敏、盛洪、樊綱、趙人偉、李實、張平、鄧正來等審讀,他們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見,同時,還與秦暉作過討論,特此致謝;但本文的觀點和錯誤當(dāng)由筆者負責(zé)。 |
|
|
| 新浪首頁 > 財經(jīng)縱橫 > 觀點分析 > 張曙光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新浪網(wǎng)財經(jīng)縱橫網(wǎng)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wù) | 聯(lián)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wǎng)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chǎn)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