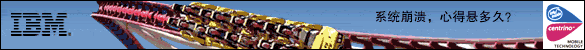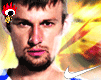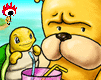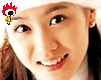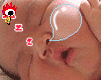|
汪丁丁
另一位汪家的先生在《讀書》呼吁研究“關鍵詞”,有兩位先生 還編了兩個“關鍵詞”的解釋,編輯部稱為“詞語梳理”。(見《讀書 》一九九五年第二期)這些,都是好主意。西學興起之后,中國人接觸 此類“關鍵詞”日多。由于漢語的特殊功能,再加上此時此地中國的 特殊環境,人們對“關鍵詞”的理解,頗多偏離原義之處。偏離無礙 ——有時還
要“誤讀”呢!——但要知其之所以然。現在為了響應這 一位汪先生的號召,試以若干最常見的“關鍵詞”,謅出一篇經濟學 之概說,也就是供中國一般的知識者——我假定他們都是《讀書》的 讀者——了解的對人類社會最基本問題的經濟思考。也許,這也是了 解“關鍵詞”的一個辦法。
經濟學是什么?它應當是什么?這當然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從本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經濟學就被認做是研究如何有效地、用有限的手段(means)去應付人們無限止的“欲望”。不錯,我用了“欲望”(desires)而不是通常所用的“目的”(ends)。因為我要用“目的”來表達那些更高遠的精神指向。另外,我用了“應付”(meet)而不是通常翻譯的“滿足”,因為我們正是在“應付著”那些永遠無法滿足的“欲望”(我不知道什么時候人類才能進入“各取所需”的社會)。分工和專業化迫使經濟學家不去過問那些手段和那些欲望是否正當或是否高尚。他們把這些問題留給了那些還沒有從蘇格拉底或柏拉圖那兒放逐出去的、依舊很高尚的道德哲學家們。經濟學家們也不再關心人的欲望是怎么產生出來的這類問題,那已經分工給了心理學家們(理論的和實驗的)。于是現代經濟學變成了主要研究如何有效運用現有手段的科學。至于經濟學應當是什么,我想在文章的結尾處再提及。現代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就是馬克思眼里的“庸俗經濟學家”,他們是邊沁(Bentham)主義者。他們說,實際上是他們的先驅者邊沁說,凡人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滿足就感到焦慮和痛苦,幸福就是從焦慮和痛苦中獲得一定程度的解脫。在這方面人與動物無異。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一個美好社會于是應當“使最大多數的人獲得最大程度的幸福”。這句話給后代的不同意“效用主義”的政治哲學家們帶來的焦慮和痛苦直到現在也還無法解脫。記得在試刊的《三聯生活周刊》讀到樊剛自稱是“一個俗氣的經濟學家”,不禁失笑,感到了經濟學的反諷。芝加哥大學的利奧·斯特勞斯據說被目前半數的美國政治系掌門教授們尊為“先驅”,這個把哲學還給了政治學的人說過:最好的社會制度之所以實現不了,歸根結底是由于我們的二元人性,人是介于獸和神之間的“in-between being”。(Leo Strauss,What Is Politictical Philoso-phy?,Free Press,1959)那些能夠緩解人們焦慮與痛苦的東西,應當被叫作手段。所以在眼下的世界,錢是一種手段,因為用錢可以買到我們欲望著的東西;所以在那個點石成金的故事里,黃金絕對不是手段,因為他用黃金買不到任何他真正欲望著的東西。水和空氣,當它們充滿著我們時,它們就不是手段,因為我們感受不到因缺少它們而有的焦慮與痛苦;當它們變得稀缺時,它們就是手段,因為我們的生命感到了那種窒息和由此而起的焦慮。詩和面包,它們稀缺的程度是一樣的嗎?對中國大多數已經脫離了“溫飽狀態”的人來說,面包已經不值得焦慮了,代之而起的也許是住房的焦慮,出國旅游的焦慮,家用電器,汽車,養老金(未來的面包),權力欲(“自我實現”的欲望)和社會地位(對“受人尊重”的欲望),最后,如果還沒有被淘汰,我們會“欲望”聽一首好詩,看一幅好畫,賞玩一塊石頭,或其他的能夠把我們經歷過的美好的轉瞬即逝的心靈感受凝固于其中的東西。說實在的,我們忙著上班下班吃飯洗漱睡覺打電話拜訪公婆父母子女上司結婚和離婚,實在沒有時間玩味我們心靈在某一瞬間的感受。像久久不品茶一樣,我們漸漸會忘記了我們的心靈,忘記了怎樣品味一首詩。習慣了沒有詩的生活,我們不再感到沒有詩的焦慮。詩,便不再是手段。失去了人生目的的人是多么容易成為手段的奴隸啊。我匆忙地穿過香港中環的鬧市,極少有機會憶起但丁的名句:“在我人生行旅的中途,我迷失在一片不毛之地”。
因為手段是那些稀缺的可以緩解我們焦慮與痛苦的東西,具有理性的我們便去追求手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焦慮與不同的痛苦,有同樣的但可以是不同程度的焦慮與痛苦。因為手段是稀缺的所以有著不同程度的焦慮與痛苦的人們對同一個手段感到不同程度的需求。如果我剛剛帶著一片面包走出了干渴的大沙漠,我需要水猶如那個擔水叫賣但饑腸轆轆的老人需要我手里的面包。交換,亞當·斯密說交換是人類的天性。交換水和面包,可以解脫我們雙方的痛苦。總量不變的手段,僅僅由于交換,滿足了更大多數人的更大的需求,這是一種改善,一種有利于一些人而不損害任何人的,經濟學家稱為伯累托改善的事件。交換是實現“伯累托改善”的合乎人類天性的方式。理性的人追求手段的活動包括生產出更多的手段。于是為生產更多的手段所需要的那些東西,即投入品,也變成了手段。土地和勞動力是生產面包的投入品,于是有了對土地的追求和把勞動力視為手段。時間,這是解脫一切痛苦所必須的“投入品”。所以時間是手段。用手段生產手段,一直到那些最原初的手段,我們的“知識”找不到任何方式可以用任何手段去生產出它們。這些原初的手段叫做要素。時間就是一種要素,因為人類,除了幻想中的“時光機”,尚且不知道怎樣生產時間。從終極意義上說,世界上只有人類時間可以稱做要素。其他要素之有限性蓋源于人類沒有足夠時間去發現更多的資源。
對于稀缺的要素,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想辦法節約它們。對時間的節約是最重要的節約。那個全知全能的上帝如果允許我猜測的話,我猜上帝一定正在注視著人類以她在地球上生存的最后這幾百萬年(或幾十年)的時間竭力生產著她稱為“幸福”的東西。這個生產方式的主要特征就是人類物質勞動時間的節約。交通工具是為了節約步行的時間,機器是為了節約手工的時間,學校是為了節約重復體驗同樣的經驗的時間,警察節約了所有人打架的時間,市場節約了交易雙方互相尋找的時間,甚至還有(如果不是不敬的話)——家庭節約了求偶和生產健康人類的時間,神父節約了人們研究圣經的時間……分工,上帝看到的是人類通過分工來節約時間。操作交通工具和機器的人,教書的人,當警察的人,商人,男人和女人,當神父的人。這個社會里的“人”不再是單個的抽象的人,而是由交換關系連接起來的分工的具體的人。每個具體的人干一樣具體的工作并積累關于那件工作的具體的知識,發明節約他的勞動時間的工具和工作組織。一個具體的人異化成了一個專業化的人,一個技術的人,通過專業知識的積累,人類做為一個整體,消耗在每一件具體工作上的時間大大地節約了。這就是規模經濟,一個人通過交換,為許多人提供同一個手段,因此他必須大規模地,從而可以專家式地提供這種手段。他在昨天獲得的專業知識被疊加到今天,昨天和今天積累的知識再被疊加到明天,如此積累下去,連同他創造的工具,他的勞動時間便越來越節省,他能夠提供的手段越來越便宜。交換關系越發達,通過交換關系安排給每個人做的工作就越具規模。這是一枚銅幣的兩面,一面是人均收入的增長,一面是財富以資產和知識的方式積累。這就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基本原理,只不過用現代語言敘述。理性的人們通過分工增加能夠應付他們欲望的手段,即財富。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要實現這可能性,兩個制度條件必不可少:(1)分工造成的規模經濟的好處必須適當地分配到每個參與了分工的人。(2)由大范圍交換關系產生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必須能夠被規模經濟的好處抵償。當市場擴大時,不確定性也變得重要起來。香港街頭的報紙販子在進貨時非常小心地估計當天報紙的銷量,盡管如此仍然有些日子剩下幾十份甚至上百份賣不出去的報紙。如果賣出一份四元錢的報紙掙一元(即批發價三元),則每剩下一份報紙就相當于白賣了三份報紙。若剩下一百份就相當于白賣了三百份。所以報紙的批發與零售價格之差必須足夠大,可以抵償不確定性造成的損失。否則就不會有人分工做報紙零售業。保險公司通常允許它的保險推銷員獲得每一份人壽保險的零售價格的百分之五十的回扣(例如紐約人壽保險)。如此高的零批差價是因為推銷保險不確定性極高。通常一個保險推銷員需要訪問四個推銷目標才能賣出一個保險合同。不確定性還來自激烈的競爭。即使只有兩個競爭對手,價格戰、回扣、心理策略、資產兼并等等,都會大大提高虧損的風險。因此競爭對手的穩定的聯合可能成為大規模投資及生產的必要前提。利潤與風險,是一對孿生兄弟。許多經濟制度都不能滿足上面的兩個條件。例如在“熬年頭”的工資制度下,不能指望工人有積極性學習技術,因為專業化產生的好處完全沒有分配給花了力氣專業化的工人。例如領取官俸的政府干部沒有積極性積累金融知識以使他所管理的銀行獲利豐厚,因為他并不分享由他的專業化產生的利潤。例如個人或家庭經營的“無限責任”公司難以擴大經營規模,因為虧損可能使他傾家蕩產。相比之下,“有限責任”的股份公司愿意以出資人投入公司的資產承擔高風險的大規模投資和經營。當然另一方面,出資人會擔心在承擔了高風險之后,得不到相應的高利潤回報,因為分工去追逐利潤的是那些慧眼獨具的企業家,他們不必是出資人。利潤應當在企業家與投資人之間適當地分配。如果分配不當,股份公司制度就與其他失敗的制度一樣,無法擴大分工和經濟的規模,無法創造財富。在一個不講信譽的社會里,怎樣是“適當”的分配呢?缺了基本的信任,中方“坑”外方,外方“坑”中方,中方和外方合起來“坑”政府,政府也“坑”企業,企業家“坑”資本家,資本家再去“坑”其他的資本家……所謂“冤冤相報,永無了結”。
其實經濟學家把自己局限在手段的研究上是為了與心理學家、科學家和工程專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以及其他的種種專家來個分工。在這個安排下,經濟學研究生產、交換和分配。在生產交換分配中,現代的主流經濟學分工研究交換。從最近幾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領域看,經濟學研究的方向或“研究綱領”正在改變到制度方面去,交換的制度,生產的制度,分配的制度,政治的制度,科學合作的制度,組成社會的制度,能促進和不能促進文明的制度等等。由于人人都想要過更好的日子,由于分工提高勞動時間的生產率,所以有了“經濟社會”或人類社會的經濟上的理由(人們當然可以有其他的理由聚集在一起,例如佛格森特別鐘情的“affectivity”)。社會靠了制度得以維持和發展。
研究制度的學者們追究制度的根源,認識到一切制度的維持和變化都要以運行那個制度的人所積累的知識為基礎。最典型的制度,例如交通規則。如果甲從東向西,乙從南向北,以同樣速度同時駛到十字路口,這兩人就面臨一個制度安排問題了。如果甲和乙的交通知識一致,都是“紅燈停,綠燈走”,或者“紅燈走,綠燈停”,當然出不了問題。但如果甲認為“紅燈走,綠燈停”,而乙認為“紅燈停,綠燈走”,那么不論誰面前是紅燈,一場車禍不可避免。結論:制度的基礎是參與合作(分工也是一種合作)的人們關于“如何協調彼此行為”的知識。
更復雜的制度,例如社會制度,必須建立在人們關于彼此權利的共識上。霍布斯說,人類缺乏這種共識就會陷入“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古希臘斯多葛學者說,每個人都知道這種不尊重他人的后果,這件事本身是最重要的,它作為知識,能使每個人推論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這是斯多葛學派理解的正義,也是現代的“契約主義者”如布坎南、羅爾斯、賓莫爾(Ken Binmore,Game Theory andSocial Contract,1994)所謂的“每個人都試從其他人的位置上看世界”。契約主義者從正義可以推出道德。因為“知”經過了上述的推理就是知道“止于至善”。不知道這算不算“格物明德”。
道德的敗落在任何時候都是可悲的。我指的是使社會之為社會的那些道德共識,他們構成一個社會制度的基礎。同樣,一個新的社會要想站得住,也必須找到自己的道德基礎。如前述,市場經濟不可能在人人都“殺熟”的世界里立足,除非人人都經歷過被熟人“殺”了的滋味以后知道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上帝一定覺得觀看人類歷史一幕一幕重演枯燥無比,所以常常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東西上去。每個亂世之后,人們都總結出孔孟之道,然后再把它遺忘。從前,西方人信基督教時,就不會忘記了自己祖宗的道德。哈耶克說,那些重要的、幫助了人類在生存競爭中延續下來的傳統,多數時候是由宗教守護著的。(《致命的自負》,章九)就這樣,我寫出了經濟學上若干關鍵詞。對任何理論的把握都是通過對重要概念的理解實現的。對重要概念的理解在對話中表現為對關鍵詞的解說。欲望、手段、要素、稀缺、信息、交換、分工、規模經濟、分配、伯累托改善、知識、權利、正義、道德和宗教,這些就是這個經濟學解說的關鍵詞。寫給思考過經濟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讀書人,并且故意“空”了許多該寫但未寫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