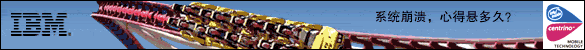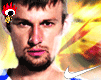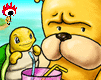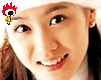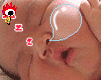| 知識過程與人生感悟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6月11日 14:17 中評網 汪丁丁 | |||||||||
|
汪丁丁 理論,在消費主義的時代,便成了消費品。 年輕又有才華的理論家,骨子里總是對“以前”的理論懷有不屑一顧的輕視。因為凡是“以前”的理論,必定已經有聰明人繼承過和批判過,從而生出了新的理論路向與新的理論
能夠意識到理論局限性的人,和想要超越一切可以超越的人,當然是有才華的理論家,當然不必是把理論當做消費品的理論家。在什么樣的前提下,理論就成了“消費品”呢?當我根據了其他人的見解,尤其是根據了“專家”意見,被告知某某理論的某某局限性,從而相信那理論是我不必去理會的時候,那理論便成了我的“消費品”。這里出現的首先是權威性的專家的反思性的意見,其次是專家為理論貼上的標簽的超越自我經驗的含義。這兩點其實已經構成了吉登斯所說的現代性的三種驅動力量之最重要的一種(<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第一章,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把理論當成消費品的傾向,只不過是消費主義時代“精神生活快餐化”的諸種現象之一。經濟發展的結果總是提高了人的勞動生產率,從而勞動時間的市場價值日益提高。一方面是精神生活的投入品(書刊,影視,聲樂,旅游,...)的多樣化與專業化,一方面是消費者的時間價值的增長,這兩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驅使消費者放棄普遍性的學習,轉而依賴專家經驗,由專家替消費者來挑選精神消費品。在學術前沿的研究者與大眾之間,出現了一群中介人,他們的社會分工是把學術轉化為大眾消費。于是當中國進入九十年代后期時,分工生產“精神快餐”的報紙期刊的編輯們開始成為替大眾讀書的人。 可是精神消費的這種“平面化”傾向是對精神生活本身的消解,而精神生活的消解意味著生活意義的喪失。這后半句話的邏輯還可以這樣展開:一方面,任何人生意義都需要通過真實地去生活過,才可能感悟到。而“生活”是專家無法替代的,“專家經驗”對于沒有生活過的人來說不算是經驗。另一方面,生活與對生活的理解是不可分離的,沒有感悟到的“生活”對生活著的人來說不算是生活。 知識,僅當它被當成一種過程來把握時,才具有個人意義。我的論證分為三段。第一,當我有所感受并且感到有沖動要表達這種感受時,我的具體感受便進入了“符號”表達的階段。可是轉化為符號的感受,為了讓別人理解,不再是特殊的感受;符號所指的感受必定是“感受類”---概念的生成。具體感受的概念化是主體之間的“客觀性”,所謂“主體間性”,具有意義的必要條件。這句話的另一種表達是:為了避免陷入“唯我主義泥沼”,我有沖動要說出我的感受,通過我與他人感受之間的“主體間性”來認定我的感受的真實性。這反映的是各個局部知識之間的“互補性”特征,被我稱為“知識沿空間的互補性”(與休謨的因果性聯想對應的個人感受的真實性問題所涉及的知識性質,被我稱為“知識沿時間的互補性”;叔本華<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附錄;汪丁丁,“知識沿時間與空間的互補性以及相關的經濟學”,<經濟研究>1997年6月)。因此個人知識的真實性的確立,與“經驗”的主體間性有關,或者更確切地說,與知識的互補性有關。這是我們將幻覺與真實區分開來的唯一途徑(除非存在著“集體幻覺”)。 第二,即便是個人知識,在特定的局部所獲得的經驗,為判定其真實性,也必須反復出現才是可信的。這是休謨所論的作為經驗科學之基礎的“因果性聯想”問題,也是我所謂“知識沿時間的互補性”問題(此處可以表示成“貝葉斯后驗推斷問題”)。但是基于知識沿時間的互補性所建立的個人經驗的真實性,正是“實踐”過程的一部分。 第三,這實踐過程的另一部分是各個局部上的個人經驗之間為確立經驗的共同性所發生的“對話”過程。這對話必定是一個過程,理由在于,如第二點所論:個人經驗的真實性必須沿著時間維度才可以確立。 所以,對個人而言有意義的“知識”,是一個不斷確信(或不斷懷疑)的過程。我的論證當然很接近康德(更接近黑格爾)的“普遍主義”論證方式,但它也很接近,或者干脆就是基于經驗主義的論證方式。而這樣一種溝通正是我所尋求的。這樣一種對知識的理解,我叫做“作為對話的邏各斯”。 我相信,必須把作為邏各斯諸種含義之一的“理性”,從康德和休謨那里,推返至前蘇格拉底哲學所闡明了的“作為對話的邏各斯”,才會發生歐陸思想與英美思想在知識論上的溝通。 理論是對經驗世界的建構,理論需要知識的真實性做為世界建構的基礎。因此理論依賴于知識過程,從而“理論”自身也是過程。當我們把“理論”當成消費品的時候,恰恰抹殺了理論過程。沒有過程的理論,充其量是簡化論的理論;而考慮理論的發生過程,就是強調世界的復雜性和不可化約性。 在知識的分立或知識分工當中,如同在任何分工當中那樣,包含了這樣一個基本的內在緊張:一方面,不投入到特定的局部里去的人是無法獲取任何知識的;另一方面,投入到特定局部里的人不得不依賴于其他人(在其它局部里)的“專家經驗”。也正因此,“作為對話的邏各斯”才有生命。 作為“對話”的邏各斯,其生命力的源泉在于我們每一個人傾聽他人的意愿。然而我們自身的話語權力總是扭曲了我們的傾聽。“熱愛生命”,這并不意味著傾聽的意愿;尼采理想里的“超人”似乎并不傾聽什么。但是要對生命有所感悟,就必須傾聽;完全不傾聽別人感受的人,甚至無法分辨自己的生命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生命的動詞是生活,是被當做一個實踐過程的“生命”。我們熱愛生命,因為它是真實感受的唯一來源。 知識過程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并且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談論“我們”(通過對話形成的“共相”)。列維那斯說:海德格爾的問題---“為什么不是什么也不是?”應當被替換為這樣的問題:“我生存的根據在哪里?”(E. Levinas,1981,“Ethics as First Philosophy”。)我的問題是:在“沉默”與“對話”之外,是否存在著“我生存的根據”呢?有人爭辯說:人們之間總存在著更加一般的,叫做“關系”的東西,不管他們是否相互認識和對話。我不同意,因為“關系”本身是被理解著的“共相”,而任何共相都需要“他人作為我的根據”。作為我生存的根據的“他人”,正是經由“對話”進入這一根據的。而沉默,固然遠比“說”要意義豐富得多,卻歸根結底是由“對話”襯托出其意義的。如果我不知道說的意義,我就不知道“沉默”意味著什么;當我說的時候,我才明白了“沉默”意味著我沒有說的一切。 沒有“過程”的知識好比互聯網主頁索引,或者圖書館分類卡片,那只是別人(專家)做的有關世界的一個“分類”。如果我僅僅關心完成老師布置的課外作業并且完成作業的唯一目的是得到學分,那么我可以把整個圖書館存儲的這些知識當做“消費品”來使用,我只須查找作業里面的關鍵詞,按照卡片索引提供的文獻號碼查找文獻,抄錄文獻作者們寫過的與關鍵詞有關的句子。我把這種做學問的方式叫做“不思的史學”方法,因為我確實觀察到許多留學生以及美國的大多數中學生們使用這樣的方法,將學問變成了日常程序的一種,與吃飯,游泳,和看電影并列。 可是“生活”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生活不是專家分類,至少不應當成為被專家“分類”的生活。對人生的體悟要求著作為“過程”的知識。有關我們每一個具體的人的“個性(individuality)”的生活體悟,不僅與個人的生活經歷有關,而且與個人所卷入的“對話”有關。由于我們生活經歷的千差萬別,沒有任何專家分類可以規劃我們每一個人的知識過程。 生活是自己的,知識過程是自己的。而知識過程的極限,是信仰。我們無法知道作為整體的知識。我們的心智,靠了作為局部知識的個人知識過程與人生體悟的啟迪,有能力去信仰。我不能夠把這信仰符號化,因為任何符號(上帝,神,...)都不確切。關于信仰,我能夠說的只是:當你意識到知識過程的極限時,你便獲得了信仰。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觀點分析 > 汪丁丁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