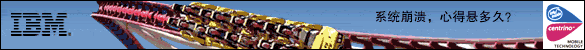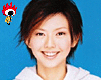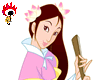| 學術分科及其超越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6月11日 14:13 中評網 | |||||||||
|
汪丁丁 黃平:談學術危機問題,可先從學術分科談起。學術分科當然有 其必要性和必然性,是學術積累和推進的重要保證,但它也不可避免 地帶來了一些問題,如由研究視野和方法所決定的具體學科的局限, 而這種局限往往妨礙著我們對一些整體性、共同性問題的把握。比如 “現代性”問題,就很難說僅僅是一個經濟學或社會學的問題,實際 上它涉及到許
汪丁丁:學術分科制度是西方學術傳統的重要方面,從亞里士多德至今已有悠久的歷史。在中國,自清末廢止科舉引進西方學制以來,如何將西方的教育和學術分科制度融人中國本土社會,一直是一個危機重重的問題。西方的學術分科制度與中國的學術傳統是格格不入的。中國傳統學術以史學知識為主要內容,以歷史敘事為主要話語形態,不注重邏輯上的合理性。科舉制要求舉子掌握的辭章義理,通達古今之變、天人之際,無所不包,的確非常綜合。分科制度下的學術則表現為科學敘述,強調邏輯合理性,與中國傳統學術在思維方式上是截然不同的。對于西方人來說,科學敘述和邏輯分析的分科制度是亞里士多德以來天經地義般的傳統,更有基督教“神召”(Calling)或“命定”(Predestination)傳統觀念的長期熏陶,使學者們甘愿在某一細小的專門學科內安身立命。但對于中國人來說就顯得危機重重了。一方面,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沒有西方的宗教感情,他們的心永遠是中國心,總想打破這種束縛人的專業分工,使學術分工制度在中國立足生根非常困難。中國人做學問的方式是靠歷史敘事,先列舉三代故事、先秦典籍、二十四史一路下來,然后續上你的當代敘事一小段,這樣你才能得到自己內心承認的合法性,也只有這樣才能夠建立起大家公認的正統性權威。在擁有這種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的群體中,要建立西式的以科學敘述為基礎的學術分科制度是十分困難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學的發展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記得一九八五年《經濟研究》編輯部開過一個座談會,主題是如何防止中國經濟學的低水平重復制造。當時引起大家普遍警覺的問題,一是經濟學文章不講究互相索引,不注明出處,根本就沒有知識產權之說,你的觀點我抄過來就是我的,發表的文章到處都是低水平重復。沒有規范的索引制度,知識沒辦法積累,沒辦法判明哪些是舊知識哪些是新觀點,學術不可能進步。只有建立了索引制度,把索引過來的別人的東西講完了,然后逼著你講出自己的東西,這樣才能使自己站在前人、別人的肩膀上,一步步地把學術推向前進。當時引起大家警覺的還有一個問題是,每一位經濟學家都構造一個理論體系,跟黑格爾似的,百科全書,無所不包。在經濟學領域,同時滾動著許多宇宙,看似繁榮,其實是低水平重復,人家一腳就把你踹了。問題是為什么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獨立體系,一個大宇宙?關鍵還在于前面講的中國的傳統,中國人的思維和敘述方式。這種傳統是很難打破的,你必須有意識地使自己服從學術分工,切忌將有限的時間和心智投入所有的領域,這樣才能擺脫中國傳統的束縛。當然學術分工需要索引等一系列制度才能真正實現知識的積累和進步。進入學術分工以后,你又面臨著如何超越分工的問題。人始終是在接受必要的限制和突破限制之間掙扎斗爭的。如果不能超越分工,你就會隨著分工的趨勢越走路越窄,最后變成學匠,沒有思想或產生不了思想。你所在的群體很可能就會淪為能夠出思想的學術中心的學術殖民地,很難避免后殖民的命運。上次臺灣有個學術代表團來這里,說他們那里沒有《讀書》這樣的刊物,能夠聯絡著較為穩定的能獨立思考的作者群,組織和發表一些提出和闡述問題的文章。還有一個值得專門闡述的問題,即學問與人格或問學與做人的關系問題。為什么一些知識分子——他們其實只是技術型專家,不再有人文關懷了——甘愿被后殖民化呢?為什么他們不再追尋自己的學術人格了呢?恐怕也與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有關。很多人從北美拿學位回來,忙于謀生,要當一個體面教授。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為先,老婆孩子熱炕頭,先把炕頭熱起來再說。這樣在不知不覺中,學術人格沉淪了,和一般勞動分工中的勞動者毫無二致,一心一意地做著學術分工制度的奴隸,樂此不疲。 黃平:他可以做成一個很能干的奴隸,像韋伯所描述、分析的官僚制中循規蹈矩的官員。在官僚制或科層制下,付一份工資,干一份活。韋伯把標準的官僚描寫成鐵籠子里的人,坐在辦公桌后面,按章辦事,但是沒有思想。這種官僚當然好,咱們現在就缺這個,咱們中國的官僚太通人情世故太老謀深算了。但將學術和學者都納入這種官僚制就有問題了,然而現實正是這樣:大學給你錢,給你房子,然后你就按欽定大綱講義,開始一遍遍地復制知識。這樣作為學者的本真的生存就被遮蔽了。 汪丁丁:所以我們說為學與做人之間是有深刻的內在關系的,你必須有膽識與能力從威壓與引誘中使自己獨立超脫出來,有意識地將自己邊緣化,你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 黃平:你必須不斷將自己擺脫出來,將自己退到遠處(列維-斯特勞斯寫過一本書,書名就叫《退到遠處去看》),只有這樣才能有對自我的反思,也只有這樣才能有真正的自我。不然就談不上超越,你只能做個分工制度下的齒輪、螺絲釘。 汪丁丁:所以學術人格問題對中國學術傳統的重建或社會科學的本土化(這里的“本土化”概念與以往關于這個問題大討論時期大多數人所持的觀念不一樣,我們這里是指將源于西方的社會科學如何融人中國社會和中國學術傳統)過程至關重要,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雙重的問題。一方面,一位學者作為中國人,不是西方人,他不可能做到或很難做到為學術而學術,因為這種神授天職觀源于西方宗教倫理。中國沒有大科學家,原因很可能出在這里。另一方面,雖然中國沒有出大科學家,但卻盛行科學主義,本世紀以來形成了濃厚的科學主義傳統。幾乎所有的搞自然科學的人都在試圖把中國的社會進程當成洲際導彈、人造衛星來設計和控制,醉心于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為什么呢?因為他們不安分,不安于自己的職業本分,總想將他們熟悉的科學方法推廣應用到整個社會領域,動輒設計出一次性改造整個社會的方案,總以為世人皆醉,唯我獨醒。這種傳統始自二十年代丁文江等人的科學人生觀,主張人生科學化。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出不了大科學家的原因也正是科學主義大盛行的原因。這是一個中國學者或學生在成為學術分工制度下的一員時所遇到的第一重困境。中國學者面臨學術分工的第二重困境是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中國人興西學實際上是近代落后挨打的結果,是不得已而為之。在一次次敗給列強的船堅炮利之后才逐步開始學習西方的一套,開始向西方社會或近代社會轉型,這種社會轉型是一項艱苦而漫長的工作,需要大量工業知識的積累。你看日本和西德二戰被炸平以后,為什么能在極短時間內恢復?Gary Becker解釋這主要是人力資本在起作用,因為戰爭摧毀的主要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則是基本保留下來的。這些豐富的人力資本在戰后合適的政策和有利機遇等條件下,很快就重新繪出更美更新的圖畫,使日本和西德很快地廁身于主要工業強國的行列。GaryBecker動態數學模型解釋得很清楚:物質資本盡管損失很大,只要人力資本保留到一定程度,在直角坐標里,動態演化的結果必然會達到高收入均衡;如果人力資本摧殘到一定程度,如教育失敗等,物質資本盡管十分豐裕,動態演化的結果也會趨于低收入均衡。可悲的是我國戰亂后在某種程度上經歷的正是后一種情形。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是以中世紀后期(約十一世紀)開始的工業知識的逐步積累為基礎的, 包括引進中國和阿拉伯等地的工業知識,經過四五百年的積累,其中有無數次偶然的匯合,最后實現突破,發生了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所依賴的這些工業知識,需要大量非人性的異化的分工勞動。而“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藝術人生則是不行的,必然碰壁,只能挨打,挨打了以后也只能跟著西方人異化,扭曲人性,掌握必要的工業知識,才能在現代國際社會立足。總之,繼承著自己文化傳統的現代中國人,在現實生活中不得不去經歷西方式的技術的人生。這是中國學者在面臨學術分工時的第二重困境。回顧晚清以來中國學術傳統的重建工作,可以說是非常失敗的。因為作為學術載體的、有穩定政治經濟地位、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共同體未能發育起來。一方面學者們受生存問題困擾,不得不服從學術分工,甚至連服從分工也滿足不了生存需求,只是近幾年腦體倒掛才有所扭轉。另一方面,學者們學術人格失落,知識分子斯文掃地,可謂久矣! 黃平:如果我們回溯到清末科舉改制以前,傳統中國的士大夫倒有穩定的政治經濟地位,而且以社會精英、良知、文化的象征自居。廢科舉時,沒有相應的配套制度改革,后來表面上雖然出現了自由漂移型知識分子,但實際上并沒有形成保障知識分子地位和尊嚴的制度。由于廢除科舉時過于倉促,以后則陷于長期的內戰和外敵入侵,天下太平了以后又是人為的內亂,原來的知識分子保護網沒有了,新的保護網又一直沒能建立起來。到了四十年代又宣布了知識分子本身就有問題,是骯臟的,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先秦子以來傳統士大夫的“為天地立命”、“為帝王師”,自信真理在手的心理優勢,其文學人格與政權的相對疏離狀態,批評政治生活的清議傳統從此都不復存在。 汪丁丁:這些東西到了廢止科舉以后全沒了制度保障。到后來新制度穩定下來的時候,你又成了毛了,灰溜溜的,變成了行政機構的附庸。這種體制狀態下很難產生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精神,這是中國文化和學術,甚至包括國畫創作衰落的原因之一。本來中國畫講的是意境,意境的根底是什么呢?是終極關懷,你有特別高的追求,才能出來意境。你平白無故地畫山水就只是匠氣。 黃平: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雙重的,一方面學術分工沒搞好,根本沒實現細膩的專業分工,離合理規范分工要求還差得遠呢!分工原本要求什么呢?具有使命感,服從神賦天職,你把你的分內事作好,在專業范圍內追求完美,這才叫為藝術而藝術、為學術而學術,做匠也要做高級的匠。米開朗基羅最先不也是匠嗎?但他有使命感,最后成了大家。我們現在在這方面還差得遠。與此同時,像你剛才所說的,沒出大科學家卻又是科學主義盛行,科學主義只學了點皮毛,卻成了遮蔽人生、使人片面化非人化的東西。另一方面,雖然在專業領域沒有做出絕活,而學者們卻被遮蔽得一塌糊涂。總之,晚清以來的學術和教育改革總體上來說是很不成功的。二、三十年代以來雖有一些人作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一些人在某些領域內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由于教育和學術改革總的方向是科學主義,傳統的東西已被棄之一旁。 汪丁丁:學術分工制度一旦形成以后,那就是制度復制人,人復制制度,日益走向極端。你看大學原有國學門,文史哲可以兼通,后來呢?越分越細,歷史就分古代史、近代史、世界史等等,有的一輩子就搞禁煙運動、保路運動,別的則完全不知道了。通才沒有了。 黃平:馮友蘭說他解放后到七十年代末就認真寫過兩篇文章,結果都招徠了全國性的大批判。有一篇就講大學是培養什么人的(另一篇講抽象繼承)。他說如果大學培養不了通才,又培養不出高出(或至少不低于)平均水平的專才,那大學還剩什么呢? 汪丁丁:從我們這一代開始,可能還要更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都立志做科學家,做華羅庚、陳景潤,結果是既沒有出大科學家,而我們的生存狀況卻被設計和異化成不成樣子。學術人格是講求獨立的,要求和政治權貴及商業富豪保持疏離狀態。權貴和富豪這兩種力量總要千方百計擠壓學術自由空間。獨立的學術人格共同體的形成需要具備許多條件,我上次在《讀書》上談過(見《讀書》一九九七年第七期《“學術中心”何處尋?》——編者注),除了體制障礙、市場需求的約束之外,目前我國出版界的現狀、學術界的道德水準等也都阻礙著獨立學術人格共同體的發育成長,影響著學術的繁榮。如學術界知識產權的尊重和保護的意識較差,有的人寫出的文章著作不敢交給編輯,怕被剽竊。學人之間道義上聲援支持也沒有。這樣一方面學者們生存都很困難,又沒有相應的支持因素,要建立獨立的學術人格共同體是很困難的。北京在這方面相對理想一些,有較好的學術傳統,有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的規模聚集效應,信息靈通,外地的學者則要困難得多。 黃平:從現代意義上來看,知識分子可分為幾類:一類是技術型專家,第二類以批評現實生活為使命(相當于中國傳統的“清議”?)。現在我們還需要第三類,那種能對學術本身、對他自己本身進行反思的知識分子。這種人能反思學術分工的必要性及其缺陷、危險性,能不斷地跳出來站到遠處去反觀自己,因此能不斷地發現問題。只有具備了這種反思能力,才能不斷地有意識地從自己所在學科跨出來與其他學科的學者進行對話,甚至和作為研究對象的當事人,比如說工人、農民、小販進行對話。而按照胡塞爾的說法他們正是“生活世界”,是學術的真正來源和最后服務目標,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學術世界只是人為的用學術符號和規范再構的世界,里面看到的都是經過主觀選擇的、分析過的東西,不再是生活世界的原樣了。這些學術規范相當于過濾器,濾掉了生活世界中許多有血有肉的東西。你如果沒有反思的眼光,以為經過過濾后呈現給你的就是生活世界真實的原貌,沒有學術警醒,那就會出現偏差。 實際上,學術分工是社會勞動分工的一部分,勞動有百業,學術有百科,分工是現代社會難以避免的趨勢,陶淵明式的生活方式是行不通的。但學者進入學術分工后又必須保持必要的警醒,不為分工所框死,要能不斷地從所在分工領域站出來到別處看,先憑著濾鏡所看不到的東西,看到生活世界本身。這樣你有你的范式,他有他的范式,相互比較借鑒,從而超越分工障礙。所以學術分工既可以是擋住我們視野的屏障,也可以成為超越分工的橋梁。本來現代人進入學術分工與進入一般勞動分工表面上看并沒有什么區別,無非是在既有的學術分工體制下謀生,工作要求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可能做得很好,但他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只是復制,沒有創新。要真正推進學術,除了真正做好本職工作外,還必須有創造性的活動,真正體驗創造的喜怒哀樂。既要能進入分工而且能做好,又能不斷超越,不斷地反思,這樣也就進入了創造性的美學人生。當“荒謬”、“痛苦”這些概念進入哲學的時候,實際上又回到了前蘇格拉底哲學,揭示了創造性美學人生的本來面貌。哲學在古希臘語中是“愛智慧”的意思,智慧就是指我們所體驗的生活不是簡單地重復已發生過的一切,而是我們在其中發現了別人未發現的東西。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象形文字也照樣有遮蔽,所以中國文人醉心于書法,醉心于禪悟,以抗拒遺忘。文字、語言本身都是有遮蔽的。 汪丁丁:關于語言的遮蔽,鄧少芒一九九四年出的《思維的張力》一書前幾章對從柏拉圖開始的語言的“顛倒”過程進行了闡述。語言的顛倒功能在亞里士多德哲學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本來質料(matter)是在先的,古希臘人對用事物類別的認識習慣于枚舉法,如“人”這個概念是用張三、李四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集合來表示的。深受生物學分類法影響的亞里士多德用抽象的類概念來給事物分類命名,結果逐漸演變成先有一個抽象的概念、理念,然后才有一個個具體的事物,具體事物只是無限的理念在世間有限的實現,是相對的。這樣一來,語言、觀念的世界變成了先于現實世界的東西。這就是語言的“顛倒”功能。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當講到“這是一棵樹”的時候,實際上已顛倒了真實,把活生生的一棵樹歸于一個抽象的類概念之中。所以只要有語言,就可能有遮蔽。老子可能對語言和符號的遮蔽性有所認識,所以他說:大辯不言,大音無聲,大象無形。 黃平:也就是剛才我說到的,我們雖然用象形文字,但大家就是始終不滿意,所以才有書法,才有意到筆不到,才有氣勢和意境。而這種氣勢、意境只有突破規范筆劃時,才能表現出來。實際上這就是表明語言世界和生活世界是有距離的。當我們失去警覺,以為我們熟知語言世界是真實的,而語言世界之外的世界是虛假的,或根本不存在的,那我們就被語言遮蔽了。 語言本身當然也構成了自身獨特的符號和意義的世界,這方面當代的語言學、符號學有許多闡釋。就社會科學而論,至少十九世紀以來,也是被一系列概念、范疇構筑起來,大家在這個被構筑起來的世界里做文章,卻很少對這個世界本身進行反思。近年來這方面做得較好的,要算沃勒斯坦等人的《開放社會科學》(三聯/牛津一九九七年版)。一批人用幾年時間寫出這么一個小冊子,包含的問題意識和反思精神卻是很多大部頭著作所缺乏的。大部頭的上乘之作也有,如布羅代爾的三大卷,也是對被語言(概念、范疇)遮蔽了的歷史過程的再發現和再認識,可惜我們對它的重視太不夠。我始終感到,要避免這種學術后殖民化的命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學人應該明了和擔當我們的“神賦天職”(calling)。我們不信神,西方的神自然不會召喚我們,我們應該傾聽的是我們的前輩先人、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時代對我們的召喚,我們應該明了我們的使命是什么,不然我們就不可能超越,只能永遠陷身于別人給我們設定的領域而不能自拔。服從神賦天職是我們能進入學術分工,又能超越分工的唯一的動力。從港臺給我們提供的經驗和教訓來看,中國要進入國際體系,包括學術國際體系,從技術上講并不太難,難的是如何超越別人給我們設定的位置。中國文化如果再生或復興,就必須有一大批秉承神賦天職的學人的貢獻,否則就只能落個超大型文化附庸的結局。 汪丁丁:上次我們在大覺寺談教育危機與我們今天談的學術危機實際上是一回事。教育問題說淺了是物質條件問題、師資問題、應試制度問題,實質上是和教育內容和指導思想有關的。現在我們教育的目的是將新一代人培養成分門別類的專家,不是開發人的心智,所以才有眼下的考試激烈競爭、分科過早過細等問題。而在文藝復興時期,教育以開發人的心智為宗旨,是完人教育,那就不可能有這種危機。教育危機和學術危機通過制度和人的一再復制,不斷糾纏在一起,實在是難解難分。 黃平:《讀書》今年第八期有一篇何兆武的文章《也談“清華學派”》,談到以前的老清華不但是中西貫通,而且是文理兼備,當時許多著名科學家都能寫出漂亮的關于文化或歷史問題的文章。對照現實,很值得我們深刻而認真地反思:如何才能超越學科的分界與限制?
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下午于北京三聯韜奮圖書中心二樓咖啡廳, 薛松奎整理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觀點分析 > 汪丁丁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