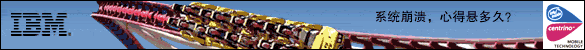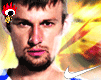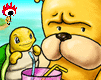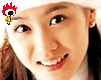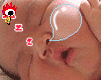| 中國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問題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6月11日 14:10 中評網(wǎng) | |||||||||
|
汪丁丁 經(jīng)濟學(xué),或任何一門社會科學(xué),當(dāng)它的“純粹”形態(tài)的普遍原理被應(yīng)用於具體社會的時候,總會引出“實踐”形態(tài)的問題。現(xiàn)象學(xué)對純粹科學(xué)的實證主義態(tài)度的批判,對中國經(jīng)濟學(xué)的意義在於:它一方面揭示出哈貝馬斯( J ürgen Habermas )曾經(jīng)強調(diào)的認知與興趣之間的知識社會學(xué)聯(lián)系,從而為經(jīng)濟學(xué)的話語權(quán)力劃出合理界限;另一方面以批判的實踐理
九十年代中國改革的經(jīng)濟學(xué)含義 90 年代初由鄧小平首先加以肯定和推廣的“南中國模式”在整個 90 年代成為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基本模式。不論這一模式有多少形形色色的版本,與傳統(tǒng)國營企業(yè)的激勵機制相比,它的制度經(jīng)濟學(xué)特征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對“分立的財產(chǎn)權(quán)利”( severance of property )的保護。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 )晚年曾對這一產(chǎn)權(quán)形態(tài)如何根本性地改善著多數(shù)公民的經(jīng)濟和政治權(quán)利進行了充分的論述。按照他的理解,這一產(chǎn)權(quán)形態(tài)以及圍繞它而發(fā)展起來的一整套支撐體系,不應(yīng)當(dāng)誤解性地遵循它在西方社會的特殊歷史被命名為“私有制”或者叫做“資本主義制度”,而應(yīng)當(dāng)被稱為“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整個 90 年代中國人均收入水平和現(xiàn)實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實質(zhì)上就是這一合作秩序不斷擴展的結(jié)果。由於合作范圍在人竤中的擴展,分工與專業(yè)化便得以深化,最終產(chǎn)生了巨大的規(guī)模經(jīng)濟效益,表現(xiàn)為勞動生產(chǎn)率和國民財富的增長。 為了在一個統(tǒng)一框架內(nèi)理解國營企業(y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和純粹私人企業(yè)的制度安排及其所產(chǎn)生的經(jīng)濟效率,根據(jù)西多夫斯基原理,我在附圖( Scitovski diagram )中給出了三組曲線來說明這三種不同經(jīng)濟制度中的“委托—代理”關(guān)系是如何表現(xiàn)出不同的經(jīng)濟效率的。 假定一切生產(chǎn)行為都可以描述為生產(chǎn)的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締結(jié)的契約關(guān)系規(guī)范下的行為,假定附圖的縱軸方向指示了委托人利益增加的方向、橫軸指示了代理人利益增加的方向,那么在代理人可以選擇的各種行動方案中,有三類是與委托人利益和代理人利益密切相關(guān)的:( 1 )那些同時增進委托人和代理人福利的方案;( 2 )那些僅僅增進委托人福利的方案;( 3 )那些僅僅增進代理人福利的方案。顯然,在主流經(jīng)濟學(xué)看來,“人類合作”的秩序可以得到擴展,當(dāng)且僅當(dāng)存在著第( 1 )類方案時。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第( 2 )和第( 3 )類方案的實現(xiàn),那些旨在實現(xiàn)第( 2 )類方案的制度不妨叫做“奴隸制度”,而那些事實上極大地鼓勵了第( 3 )類方案實現(xiàn)的制度不妨叫做“巧取豪奪制度”。出於明顯的理由,這兩種制度都不可能有大范圍的擴展;凡是違背個體自愿原則的制度,由於喪失了“合法性”,都是難以為繼的制度。由於上述三類行動方案都是代理人的“可供選擇的方案”,我們實際上假設(shè)了代理人是“有合作意愿的”。 如我在附圖中作的解釋,代理人的均衡行為模式在這里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 1 )委托人福利的增長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敏感地依賴於代理人的努力;( 2 )代理人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敏感地依賴於委托人對代理人的監(jiān)督。這兩個條件的第一個已經(jīng)包括了生產(chǎn)的技術(shù)結(jié)構(gòu)(例如大規(guī)模以及新技術(shù)的使用,生產(chǎn)部門之間的投入產(chǎn)出聯(lián)系),第二個條件則主要反映了生產(chǎn)的制度結(jié)構(gòu)(例如團隊內(nèi)部互相監(jiān)督的成本,外部人監(jiān)督的諸方式)。代理人無差異曲線與行為約束的切點給出不同契約下的均衡——作為模式的典型行為,或者代理人的“行為模式”。在附圖所示的三個切點處,代理人的不同行為模式為他自己和為委托人生產(chǎn)了不同水平的福利。對委托人而言,代理人行為約束的最高點代表了最大福利。可是由於存在著“代理人成本”,代理人的均衡行為通常不發(fā)生在最高點處,均衡點與最大福利點之間的差距就是代理人成本。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經(jīng)濟效率方面的特征性的差異就在於它們表現(xiàn)出不同的代理人成本。 在“委托—代理”的各種可能形態(tài)中,“家庭”可以被視為是與委托人、代理人的利益關(guān)系最接近的形態(tài)。家庭成員之間的分工,由於具有較小的契約監(jiān)督成本(給定生產(chǎn)的技術(shù)條件),在附圖所示的“委托—代理”諸關(guān)系中可以由最左邊的那組曲線(具有較大的正的和負的斜率)描述。 50 年代出現(xiàn)過的規(guī)模最大的“人民公社”,擁有兩萬戶農(nóng)民,其監(jiān)督成本極高,并且代理人的個體努力對“集體委托人”福利的邊際貢獻微乎其微。這樣的制度安排可以由附圖最右邊的那組曲線(具有較小的正的和負的斜率)描述。而所謂“南中國模式”,或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可以由中間的那組曲線描述。 如果生產(chǎn)的技術(shù)條件一樣,那么家庭或由最左邊的曲線組描述的制度安排具有最高的代理人生產(chǎn)效率。但是家庭經(jīng)濟能夠容納的生產(chǎn)的技術(shù)條件缺乏規(guī)模經(jīng)濟效益,而規(guī)模經(jīng)濟效益是誘致“人類合作”的秩序從家庭向外擴展的根本原因。國營企業(yè)固然使用了大規(guī)模經(jīng)營的技術(shù)條件,但其制度安排下的監(jiān)督成本太高,以致部分甚至完全抵銷了規(guī)模經(jīng)濟效益方面的好處。這兩種極端的制度安排的利弊就突顯出了為甚么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或“南中國模式”可以成為 90 年代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幾乎唯一有效的驅(qū)動機制。 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比家庭具有大得多的技術(shù)規(guī)模)之所以具有較低的監(jiān)督費用,除了因為依靠本地聯(lián)系和血緣聯(lián)系能夠提供的支持外,還由於它主要地實行了保護企業(yè)主管人員的“利潤權(quán)利”的制度。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有比較明確的追求財富增長速度的目標(biāo),所以由鄉(xiāng)鎮(zhèn)地方政府提供的對代理人利潤權(quán)利的保護導(dǎo)致了企業(yè)(計入“代理人成本”的)利潤最大化行為。 以上分析也表明,“南中國模式”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實現(xiàn)“產(chǎn)業(yè)升級”,也就是如何發(fā)展和取代國有企業(yè)具有的那種大規(guī)模經(jīng)濟的技術(shù)條件,而這一問題的解決與投資機制的創(chuàng)新和資本市場的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 改革面臨的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問題 甚么是代理人的“利潤權(quán)利”呢?為著經(jīng)濟效率而定義的“利潤”,也就是熊比特( Joseph A. Schumpeter )所說的創(chuàng)新的利潤或“價值剩余”。在奧地利學(xué)派(包括其左派人物熊比特)和芝加哥學(xué)派的奈特( Frank Knight )看來,企業(yè)家(為追逐利潤而發(fā)生的)創(chuàng)新行為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唯一源泉。所以哈耶克認為,一個社會發(fā)展其經(jīng)濟的能力歸根結(jié)柢取決於這個社會是否保護企業(yè)家的“利潤權(quán)利”,是否“鼓勵一切個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創(chuàng)新”,是否把創(chuàng)新者的利潤權(quán)利當(dāng)做憲法的核心條款來實行。經(jīng)濟自由是其他各項自由的基礎(chǔ),創(chuàng)新者的利潤權(quán)利於是成為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所謂“保護匿名的少數(shù)”原理)。 但是在那些從社會主義傳統(tǒng)體制向市場體制轉(zhuǎn)型的經(jīng)濟中,“利潤權(quán)利”沒有如同成熟西方市場社會里那樣的“傳統(tǒng)的合法性”(對“剝奪者”的剝奪已經(jīng)摧毀了這一合法性的基礎(chǔ))。另一方面,任何創(chuàng)新都首先需要對創(chuàng)新所必須的經(jīng)濟資源實行調(diào)配,在這一意義上,熊比特曾經(jīng)說過兩句話:( 1 )“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新行為是純粹意義上的借貸行為”;( 2 )“銀行家是資本主義的守門人”。即是說,創(chuàng)新者必須說服銀行家出借他們控制著的經(jīng)濟資源(在貨幣經(jīng)濟里,資源可以通過貨幣來調(diào)配)。而資源控制權(quán)的轉(zhuǎn)讓或出借,歸根結(jié)柢是“財產(chǎn)權(quán)利”的轉(zhuǎn)讓或出借。 90 年代推動了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那些風(fēng)云人物,往往必須通過政治權(quán)力轉(zhuǎn)化出對經(jīng)濟資源的支配權(quán)利,這在“南中國模式”中也表現(xiàn)得清清楚楚。於是經(jīng)濟學(xué)家們從“效率原則”的立場提出“生產(chǎn)性尋租”的概念(或“官商合理”論,或“南韓模式”)來為這樣的權(quán)力尋租行為辯護。 效率原則在“南中國模式”里,并且?guī)缀踔饕峭ㄟ^這樣一種經(jīng)濟增長方式,在整個 90 年代(以及 80 年代后期)同“公平原則”發(fā)生著沖突。這種基於“經(jīng)濟增長是醫(yī)治一切社會問題的最好藥方”的理念,即“南韓的增長方式”,是主流經(jīng)濟學(xué)家?guī)缀跗毡榈責(zé)o視這一模式下出現(xiàn)的公平問題的原因。 我們必須承認,就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中國社會而言,以及就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而言,發(fā)展總比停滯好些,并且“發(fā)展”始終是逼迫到中國人頭上來的(“西力東漸”以及人口生育率轉(zhuǎn)移產(chǎn)生的人均資源惡化);因此,我們必須為創(chuàng)新者找到“利潤權(quán)利”的合法性基礎(chǔ),我們必須提出和解決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問題。 在我看來,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面臨著這樣三個(不同但互相聯(lián)系的)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問題:( 1 )利潤權(quán)利的合法性基礎(chǔ);( 2 )勞動與資本之間經(jīng)濟關(guān)系的合法性基礎(chǔ);( 3 )政府身份及其合法性或確當(dāng)性問題(我把韋伯的“ legitimacy ”叫做權(quán)利或權(quán)力的“合法性”,而把道德共識所提供的權(quán)利或權(quán)力的基礎(chǔ)叫做“確當(dāng)性”)。 我已經(jīng)大致說清楚了“利潤權(quán)利的合法性基礎(chǔ)”問題,我不認為理論可以解決這類問題。正如黑格爾所認為的,“法權(quán)”只通過精神歷史的中介展開其合理性。普遍的腐敗,一方面是資本原始積累難以避免的“過程”( the thesis ),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對現(xiàn)實的否定過程(或批判,或 the antithesis )。這兩方面的“綜合”( synthesis ),便是對生存困境的超越。 勞動與資本的關(guān)系是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經(jīng)典的也是核心的問題。恩格斯曾經(jīng)表述馬克思的這樣一個看法:理解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關(guān)鍵在於理解“勞動—資本”這一軸心關(guān)系。傳統(tǒng)社會主義體制向著市場體制的轉(zhuǎn)型,在蘇東各國都遇到由這一軸心關(guān)系的重建所引起的意識形態(tài)危機,而意識形態(tài)的壓力又反過來抑制著市場體制的發(fā)展。 “資本雇傭勞動”其實并不是資本與勞動之間一般的經(jīng)濟關(guān)系。在許多場合存在著有效率的“勞動雇傭資本”的經(jīng)濟制度(例如美國聯(lián)合航空公司),只要“勞動”不再是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意義上的勞動,而是人力資本(智力)密集型的勞動。只是在大規(guī)模工業(yè)化階段,也就是中國目前所處的發(fā)展階段,分工與專業(yè)化不得不采取勞動的高度異化的方式——大機器生產(chǎn)將人當(dāng)做生產(chǎn)流程的零部件。隨著資本(財富)的積累和由此而來的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市場將被逐漸稀缺的勞動誘致去開發(fā)“資本密集型”的生產(chǎn)技術(shù),從而將勞動本身解放出來。如馬克思說過的,市場蘊涵著巨大的解放力量。哈貝馬斯也正是由於看到了這一解放力量,才轉(zhuǎn)而去修正馬克思的“國家學(xué)說”。勞動的解放,與“利潤權(quán)利”的合法性一樣,是一個歷史過程。中國新左派方面的知識份子似乎不打算承認這個歷史過程,於是才有了以“第二次思想解放”、“新進化論”、“后福特主義生產(chǎn)方式”等等為代表的試圖一步跨越經(jīng)濟發(fā)展的“萬里長城”的社會方案。 我們承認“資本雇傭勞動”作為目前發(fā)展階段的主流生產(chǎn)關(guān)系,但這并不等於我們不要批判這一生產(chǎn)關(guān)系。恰恰相反,我們始終認為:一個健康的市場經(jīng)濟必須有與之相應(yīng)的道德基礎(chǔ),這一道德基礎(chǔ)就包括了對現(xiàn)實市場的永恒的批判。而缺失了這一批判力量的市場經(jīng)濟(例如馬科斯時代的菲律賓),終究難以發(fā)展為成熟市場社會那樣的經(jīng)濟形態(tài)。資本的本性便是逐利,也正因此它才能夠“專業(yè)化”為創(chuàng)新的物質(zhì)載體。為了追逐利潤,資本腐蝕權(quán)力以達到尋租的目的。資本傾向於勾結(jié)權(quán)力,傾向於勾結(jié)社會的強勢集團,這在東方和西方是一樣的。只不過,這一傾向在西方受到神的(后來則是“法治”的)制約,而在東方則無制約地泛濫為馬克思說過的“東方式的腐敗”。 “勞動”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qū)還沒有成為“自為”的,這并不是說中國的勞動者不知道他們的權(quán)利(恰恰相反,舊的意識形態(tài)早就為他們灌輸了這一權(quán)利觀念)。勞動從自在到自為需要下面兩個條件:( 1 )生產(chǎn)技術(shù)從福特主義的向著后福特主義的轉(zhuǎn)型;( 2 )在政治與社會體制中建立勞動與資本理性對話的渠道。對后一個條件來說,資本與權(quán)勢集團的勾結(jié)直接威脅著理性對話渠道的建立,因為,政府必須把它的合法性基礎(chǔ)從對“勞動權(quán)利”的保護和對“資本權(quán)利”的保護超越出來,而普遍的腐敗正在迅速摧毀著這一超越的可能性。 這樣就引出我所說的第三個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問題——轉(zhuǎn)型期政府的合法性基礎(chǔ)。我在這里強調(diào)了“轉(zhuǎn)型期”的特殊性,因為轉(zhuǎn)型意味著一個政府必須不斷地同時從舊制度和新制度的道德共識中尋求建立臨時的、過渡的合法性。這是政治的藝術(shù),它的失敗則意味著社會動蕩與革命。中國的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xué)家堅持“體制內(nèi)的變革”,堅持“靜悄悄的革命”,理由在於他們希望和平地向市場社會過渡。 就目前中國社會而言,轉(zhuǎn)型期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礎(chǔ)仍然在於發(fā)展經(jīng)濟,并使多數(shù)社會成員分享經(jīng)濟發(fā)展的好處。這一點在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期中國的歷史事變中很清楚地表現(xiàn)出來。但是僅僅滿足於經(jīng)濟發(fā)展和比較公平地(通過收入再分配手段)分享發(fā)展的成果,并不能保證轉(zhuǎn)型期政府確立其合法性。因為經(jīng)濟的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要求有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中間層”,或者乾脆叫做“中產(chǎn)階級”。這一階層在經(jīng)濟上正是“人力資本”(生產(chǎn)知識)的載體,他們最直接地(在收入再分配以前)分享到經(jīng)濟發(fā)展的好處,從而成為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動者。在政治上,這一階層足以調(diào)和最上層的權(quán)勢集團和最下層的邊緣集團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沖突,從而能夠提出和維護各方都可能接受的“社會正義”并且建立理性對話渠道(或者如哈貝馬斯所謂的“對話理性”),而不是使社會分裂為“誰之正義?何種理性?”的戰(zhàn)爭狀態(tài)。 最近國內(nèi)幾位社會學(xué)家的研究告訴我們,舊體制中的權(quán)勢集團通過新體制下的權(quán)力尋租活動,正在形成一個龐大的“資本權(quán)勢”關(guān)系,或者用研究者的術(shù)語,叫做“總體資本”。由於這一資本權(quán)勢關(guān)系的形成,根據(jù)這些研究者的觀察,原本剛剛開始生長的“社會中間階層”,正在被瓦解為依附於資本權(quán)勢關(guān)系的附庸集團,或者淪落為社會邊緣集團之一。這一現(xiàn)象正表明了缺乏適當(dāng)?shù)牡赖禄A(chǔ)的市場經(jīng)濟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蛻變?yōu)楦嗟墓倭艍艛嘀涞慕?jīng)濟活動。今年年初,由北京金融界一家刊物主持的持自由主義立場的資深經(jīng)濟學(xué)家與社會學(xué)家的聯(lián)合研討會,著重討論了這一現(xiàn)象及其可能的嚴重后果。在中國,“節(jié)制資本”應(yīng)當(dāng)被賦予當(dāng)代政治經(jīng)濟學(xué)的新涵義,并且應(yīng)當(dāng)成為自由主義經(jīng)濟政策的一個支撐點。 由於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xué)在中國改革理念中的核心地位,由於新左翼知識份子對中國的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xué)的批評,由於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面臨著的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問題已經(jīng)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中國自由主義的困境與出路問題,我在下一節(jié)簡要討論這一問題以為這篇文章的結(jié)語。 “中國自由主義”的出路 感謝 90 年代后期國內(nèi)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新左翼”知識份子之間的對話,使我們認識到自由主義在中國正處於雙重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中國是一個正從傳統(tǒng)社會主義公有制向著市場社會轉(zhuǎn)型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的“憲法精神”里面,還缺乏對利潤權(quán)利的尊重,并且由於利潤權(quán)利的不受保護,整個經(jīng)濟的創(chuàng)新能力受到摧殘,這也就相應(yīng)地鼓勵了權(quán)力尋租的能力和腐敗行為。因此中國自由主義者才提倡和堅持了蘇格蘭啟蒙傳統(tǒng)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這一立場視“產(chǎn)權(quán)”——由洛克( John Locke )定義的廣義產(chǎn)權(quán),即生命權(quán)利、基本自由權(quán)利、財產(chǎn)權(quán)利——為個人自由的最根本保障,視個人自由為最高的價值,視自由市場為文明演進的最可寶貴的制度遺產(chǎn)。另一方面,中國的“市場社會”是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市場社會,這里極容易發(fā)生資本與權(quán)勢的勾結(jié),從而腐蝕市場經(jīng)濟的道德基礎(chǔ)(合法性基礎(chǔ))。因此,中國自由主義者必須堅持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權(quán)勢關(guān)系的疏離和批判的態(tài)度,堅持福柯( Michel Foucault )所闡釋的“啟蒙”——對權(quán)力的(包括作為權(quán)力的“傳統(tǒng)”本身)永恒的批判態(tài)度。這樣,自由主義在中國就一方面要對舊體制對人的奴役進行抗?fàn)帲环矫嬗忠獙π麦w制對勞動的異化加以批判。由於這一雙重的任務(wù),西方古典自由主義與西方當(dāng)代自由主義之間的分歧與沖突在“中國自由主義”這里變得格外復(fù)雜,而根據(jù)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對中國的自由主義加以分類便顯得沒有意義。也由於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這一雙重的沖突與困境,我把它叫做“中國自由主義”。 我在另外幾篇文章里已經(jīng)討論了自由主義的困境與出路,這里簡要總結(jié)和發(fā)揮一下我的結(jié)論。在我看來,若要解決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政治經(jīng)濟學(xué)問題,“中國自由主義”就必須提倡下列三件事情:( 1 )演進的普遍主義( evolutionary universalism );( 2 )作為對話的邏各斯( dialogue as shared logos );( 3 )交往的個人主義( communicative individualism )。 這三件事情當(dāng)中,第一件關(guān)涉到蘇格蘭自由主義及“哈耶克—波普”傳統(tǒng)的演進理性與康德普遍主義理性之間的某種打通或者某種中國式的折衷,以便在中國語境里討論諸如“正義”和“自由”這類基礎(chǔ)問題;第二件事情關(guān)涉到自由主義的認識論基礎(chǔ)問題,一方面,中國的發(fā)展要求培育“科學(xué)”精神,另一方面,缺乏希臘科學(xué)傳統(tǒng)的中國科學(xué)很容易蛻變?yōu)椤翱茖W(xué)主義”從而破壞了科學(xué)精神本身。回到前蘇格拉底哲學(xué)家尤其是赫拉克立特闡釋過的大眾“分享著”的和通過對話揭示自身的邏各斯,這在我看來是一條適合中國科學(xué)精神培育的思路;第三件事情關(guān)涉“個人與社會”、“社會與國家”這兩個西方政治哲學(xué)的主題。交往的個人主義不再是孤立的西方古典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而是通過對話展開了對話倫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以這一主體間關(guān)系(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 )為人格形成基礎(chǔ)的個人主義。在我看來,這三件事情都與中國人的本性有某種親密聯(lián)系,因此不難在中國社會確立其話語傳統(tǒng)。 至於加上了這三件事情之后的自由主義是否還算是“自由主義”,我不能回答,不妨就叫做“中國自由主義”吧。 |
| 新浪首頁 > 財經(jīng)縱橫 > 觀點分析 > 汪丁丁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新浪網(wǎng)財經(jīng)縱橫網(wǎng)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wù) | 聯(lián)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wǎng)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chǎn)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