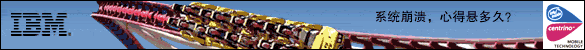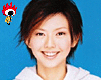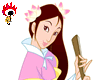|
汪丁丁
我的一位朋友,屬于那種極少有的,能夠把現實生活與一連串的 夢安排得有聲有色的人。他平均每三年改換一次“職業”,二十五年 里過了八種不同的生活,目前正在追一個新的夢——投資基金。每次 我回北京都少不了與他談各自尋找“家園”的體會。自從人類組成了 群體,人就一定已經感覺到了“異化”。個體意志通過現實的行動實 現自己的本質
。但是實現了的本質,和其他實現了的個體本質一樣, 是某種“普遍性”的實現。一旦個體意識到這種普遍性,意識到個體 的自性如何被普遍性所掩蓋,個體意志就會感到這種異化和異化的痛 苦。這是我對黑格爾“異化”概念的理解。(黑格爾,《精神現象學》 ,商務印書館,上卷,頁246-247)換句話說,只有與世隔絕才可能免 除異化的痛苦。然而,陶令筆下那個武陵漁夫離開人群,卻永遠也實 現不了他的“自性”(identity)。不說別的,兩性的分工對于延續“自 性”就必不可少。社會分工使物質條件豐富,自由意志得以實現。人 類的統一產生了巨大的實現夢想的力量,然而統一意味著每一個人都 在劫難逃。這就是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牛津大學出版社一 九九三年)所說的“終極的悖論”。據說西方人正在批判現代的分工社 會,做著“后現代”的光怪陸離的夢。這么富于創造性的夢幻世界, 首先,相當奢侈,如凡伯侖所稱,是“有閑階級”對人類做的貢獻(絕 無貶義)。其次,在西方學者看來也是褒貶不一。例如哈佛大學的珀特 爾(M.Porter)就認為這種把主要注意力從生產性轉到非生產性活動的社 會是進入了所謂“衰落的”或“財富驅動的發展階段”。(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Free Press)當然更多的是西方人對后現代主義 的共鳴。
借了西方人尋找家園的風,不少中國人也開始懷上了“鄉愁”。甘陽先生在《讀書》一九九四年十月號的文章就是一例。崔之元先生在《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四年八月號的文章更為徹底。兩位的文章大意是說,中國人沒有必要走西方人工業化的老路,應當思想解放一些,大膽創新。崔之元先生文章提出制度創新的“無限可能性”。甘陽先生的文章,在“社會科學中國化或本土化”的口號下,提出一個核心問題:“社會政治的現代轉型是否只能采取這種或那種自下而上的方式,還是同時存在著一條從社會最低基自上而下的社會重組道路?”這些提法的背景,是中國鄉鎮企業的成功。就好像當年工業東亞的成功激發了杜維明先生關于新儒家的思想一樣,不過這些提法的弱點,與新儒家遇到的困難也相似,在于對當前成功的例子還沒有充分的了解和深入地去發現問題。
研究科學的人好談“規律”,這已經被哈耶克和波普批評過了。另一方面,人文學者,特別是后現代的人文學者,喜歡幻想。圣迭牙哥加大的哲學教授博平斯(Robert Pappins)一九九一年所出新著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引羅森“啟蒙走火入魔就是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is the enlightenment gone mad)一語。“后現代的人”談“現代性危機”,無非是抱怨個體的異化(或“自治”的缺失,或“人”的被遺忘,或“地獄般的孤獨”,等等)。難怪博平斯問:為什么我們不把薩特看做對“前現代社會”的懷舊呢?實際上我讀過的后現代的東西都有忿世嫉俗的情緒。我上星期專門去聽路過香港的某權威談福柯。大致得了個印象,似乎福柯既不喜歡自由主義也不喜歡保守主義,認為正是這兩派勢力合在一起,把人們的思想自由壟斷了,把社會搞僵化了。所以“統治的失敗”(failure of governance)是非常有意義的事(福柯把一切理性的控制行為看做“統治”,個人的和公共的)。按照這個思路,“傳統”一定是不能遵守的了。不僅如此,任何思想,一旦有了權威,就要不得了。我于是又想到哈貝馬斯,他定義了完備的交流(或ideal speech situation)所要求的若干條件,其中有一個是,任何人都不能受他人思想的“歪曲性”影響。最后我還是覺得讀經濟學家的東西要干脆得多。阿羅的“不可能性定理”說(大意):當沒有人可以影響其他人時,一個群體不可能做出理性的選擇。我是數學出身的經濟學家,雖然我手上反映“想象力”的那條線(the line of mind)幾乎穿越了整個月亮丘(the mount of Moon),我試著想象一群“后現代人”怎樣組織社會,卻無論如何想不通順,除了徹底的無政府外別無他途。
旅美的甘陽和崔之元先生,在我看來是屬于“后現代”的人。絕大部分生活在大陸上的中國人,在我看來是屬于或正在屬于“現代”的人。我這個判斷的根據很簡單:你要過上富裕的日子嗎?那就必須組織社會分工。在目前中國和世界上任何地方,也許只有最大的那些資本家們可以如布勞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牛津大學出版社,中譯本,一九九三年)所說,不服從分工的要求,站在利潤的頂峰實現他們的自我。你不要異化嗎?那只好回到史前時期。我不認為后現代博大精深的各種“主義”可以被我這幾句話說倒。我下面想說的,只是整理一下一個傳統農業社會發展工業所必須滿足的那些條件。我以為這些必要條件相當于哲學上的“necessity”,或“自然律”,是沒有辦法違背的。我們不同意歷史決定論和種種“社會發展規律”學說,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胡思亂想,或如崔之元先生所說,可以無限制地創造新的制度。就特定的歷史時期而言,人類的創造性必然是受到限制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將定義工業化的“必要條件”。但是在談必要條件之前還要提一下工業化的目的。現在我們從經濟史,尤其是“年鑒史學派”的研究很清楚地看到,所謂工業革命其實是一個連續的演變過程。深層結構在長期內的演變推動著這一過程。它的可以見到的和被人們期待著的結果是勞動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從而增加了每一個人的閑暇時間。“閑暇時間”是人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升華的度量。我承認不少后現代勇士們也許愿意過一種清貧的生活,追求他們的種種夢想。但我否認大多數人愿意追隨他們,放棄追求他們從來沒有享受過的富裕生活。對后者,現代化的個人意義是非常明確的,無須贅言的。
必要條件之一:工業知識的積累過程。首先,什么是“工業”?費孝通先生(《鄉土重建與鄉鎮發展》,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總結中國農村經濟的均衡狀態是,精耕農業與家庭工副業結合的小康生活水平。精耕所以農閑時有大量過剩勞動力,所以從事工副業生產。“家庭工副業”是因為中國農村經濟是以血緣關系來支撐的。工業則不能局限于家庭范圍。“工業生產”的真義在于“規模經濟”。地利學派的龐巴沃克慣以魚網為例說明規模經濟。一個人可以赤手去捉魚,也可以先編一張魚網再以網來捕魚。如果只捉一條魚,顯然,用手比較省時間,因為編網要費去大量時間。可是若要捉幾千幾萬條魚,編網捕魚顯然有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因為編網所費的是一次性付出的時間,然后就可以捕捉大量的魚而不必再付出編網的勞動時間。這個例子說明,當產量非常大時,人類可以積累那些適合大規模生產的知識,從而找到節約勞動時間的技術。“規模經濟”就是指產量的規模,和大規模生產時可以節約的勞動時間(“經濟”的本義)。歷史上,一個家庭的消費量是不足以使用大規模生產技術的(雖然我們絕不排除在“后現代社會”里小規模生產大量品種的情況)。只是通過建立“市場”,生產者才有了動力積累大規模生產的知識并進行大規模生產(雖然中央計劃也可以命令生產者進行大規模生產,但他們往往缺乏動力去探索和積累知識)。歷史上,這些大規模生產的知識以三種方式儲存起來,(1)固化在機器里(所謂“物質資本”),(2)存入人腦里(所謂“人力資本”),(3)存在書本里(所謂“圖紙”形式的知識)。從原理上說,一旦掌握了這些知識,進行甘陽先生的所謂“后福特主義”生產(即小批量,多品種,靈活生產方式)也是可能的。所以我這個必要條件只強調知識的獲得和積累。獲得和積累知識并不容易。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匱乏正是發展中國家的本質特征。這里我們遇到一個實際問題:要進行后福特主義生產,先得積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可是沒有錢是無法置辦資本和教育人才的。于是還得先發展那些能賺錢的經濟項目,慢慢積累資本。哪些項目可以賺錢呢?就是那些具有規模經濟效益的項目。也就是說,必須先搞“福特主義”的生產。卓別林《摩登時代》里的那個工人,他當然“異化”得要發瘋,但是他一定掙著高于中國工人不少倍的工資,那就意味著他的兒子(如果社會制度合理)會接受更好的教育和掙更高的工資,那就意味著他的第五代孫可以在高爾夫球場里通過手提電腦指揮無人工廠的生產。甘陽和崔之元先生認為中國的鄉鎮企業家們正在走一條直接進入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的道路,而我認為中國鄉鎮企業的道路正好就是福特主義生產的道路。讀者看不出來哪一個觀點更接近實際嗎?
必要條件之二:協調分工的成本不能太高,社會分工才有規模經濟效益。然而分工是要有協調的。亞當·斯密認為,通常限制了分工的廣度和深度的是市場的范圍(例如一個村子內的市場需求就太狹小)。而諾貝爾獎得主貝克爾一九九二年的一篇論文則提出,分工往往是被過高的協調成本所限制而難以擴張。我覺得狗和貓如果能夠分工合作,在看守家園方面一定有非同尋常的生產力。因為貓可以爬樹,而且貓在夜里眼睛好用,而狗的攻擊力強得多。但是,畢竟他們之間的合作因語言不通而異常困難。更著名的例子當然是造巴別塔的時候遇到的語言混亂。韓國的一些企業家告訴我,他們把原設在印尼的企業轉移到山東和延邊地區,主要是為了減少文化和語言上的交流成本。香港的投資者對我傾訴他們在中國投資所遇到的最頭疼問題,是找不到合適的中方代理人。這并不是說沒有管理人才,而是指中方代理人“中飽私囊”的行為實難避免。通常數額幾百萬元的生意,是會因此而取消的。人才之間的合作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說“一山無二虎”,內斗的成本實在太高了。從歷史上說,降低協調分工的成本關鍵在于找到合適的制度。一個合適的制度下,每個人知道他在一定的范圍內有行動的自由并必須對行動負責任。“計劃”并不是這樣的制度,因為計劃者計劃的通常是他人的行動方案,因此責任與權利是分了家的。我們現在要劃清產權就是要盡力把以前分了家的權利同義務重合起來。這個重合在極端意義上就是徹底的“私有制”。但是現實中的私有制總是不徹底的,總要取決于當地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產權的歷史,取決于這些歷史或“傳統”所定義的“道德”、“權利”和“義務”等等觀念。例如中國傳統的家庭,其內部是不必劃分財產的,但不論在家庭內部和外部,都必須劃分權利和義務,自由是在“孝”、“悌”、“仁”、“禮”、“義”這些道德規范中體現的。成本較低的制度只能在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中求得,離開了傳統的所謂自由創造從來就找不到合適的協調分工的制度。這個問題與認識論有關,我已經在另一篇文章里說過了。除了制度因素外,技術因素也是很重要的。歐美許多地方的“彈性工作制”以及目前風行的企業“橫向革命”,只能建立在電訊技術發達的基礎上。總之,知識積累和協調成本,這兩個必要條件基本上概括了一個國家工業化的基本問題。所謂創造性,也只能是在這些必要條件得到滿足的基礎上進行創造。以上東拉西扯無非是說這兩個基本的必要條件只能通過相當長期的演化得到滿足。我相信,工業化道路不會只有西方社會所走過的那一條,但是所有可能的工業化道路都無法繞過這兩個基本的條件。有種說法,認為韓國和日本用三十年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路(不無爭議之處),所以中國可以“迎頭趕上”。我前幾年專研東亞經濟,對此略知究竟。簡要地說,首先,大國不能師小國,不論從基礎設施、政府控制程度,還是從外部貿易環境、國際市場潛力,中國與韓國、日本、臺灣、新加坡、香港等地都有實質上的不同。
其次,工業東亞的道路仍是福特主義生產方式,與甘陽和崔之元先生想象的鄉土經濟重建相去甚遠。我在韓國、日本、臺灣這些從前有過鄉土經濟的地方怕已不易找到后福特主義的影子。我和我那位正在追夢的朋友,我們都對市場競爭及人性的異化有著刻骨的反感。難怪人們說:“如果你在二十歲以前不信仰社會主義,你就沒有良心。”正是從這人性的高尚的一面,我們感到了烏托邦的永恒價值,和理性設計對人類社會漸進演化的永恒的威脅。懷著鄉愁,尋找家園,無可厚非——但愿我們只是懷念和尋找,而不要干擾和設計這個原本也許可以實現我們夢想的演化過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