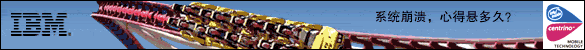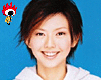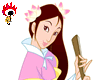| 和青年朋友談自由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6月11日 14:02 中評網 | |||||||||
|
汪丁丁 在市場社會里,人們會感到有充分的自由,同時也會感到缺少自由。自由顯然不是簡單的隨心所欲。‘自由’的真實涵義是什么呢?‘自由’是市場經濟的如此關鍵的一個條件,難怪許多年輕人在‘市場經濟’,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的號召下,要求‘徹底自由’。對他們來說,盧梭的名言:“生而自由的人卻處處被套上枷鎖”,真像是
如果‘自由’的意義很容易就可以被人把握,我們這個世界里的混亂和殘酷也許大多不會存在了。另一方面,我也不妨指出,如果‘自由’的意義很容易被人把握,‘人’在這個世界里生存的意義也許就消失了。因此我永遠也說不清楚‘自由’的涵義,我只能從古往今來數不清的圣人賢哲對‘自由’做過的探討中揀出片言只語,權當是為了能繼續說下去而找來的話題。 早期的社會契約理論家例如霍布斯,認為叢林中孤獨的一只野獸是‘徹底自由’的。徹底自由的‘人’自愿放棄一部分自由來組成‘社會’,是為了減少相互殺戮和進入一個更加文明的,物質上更加豐裕的生存狀態。于是按照這樣的理解,我們可能把自己變成一個物質生活非常豐裕但沒有半點自由的奴隸。我們當然也可能選擇做一個‘自由得一無所有’的流浪漢。換句話說,‘自由’往往并不意味著‘快樂’。正相反,自由往往意味著痛苦。我不知道對每一位讀者來說,‘自由’是否意味著‘幸福’,因為對‘幸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在希臘語言里,‘幸福’指的是那種永久性的‘美好’,而‘快樂’僅指眼前的享受。因此亞里士多德不認為某位國王是幸福的,因為他雖然畢生榮華,卻因死于謀殺而沒有得到‘善終’。不論怎樣,這種對于‘自由’與‘幸福’的理解屬於典型的西方思想傳統。我在美國和歐洲都見到過一類‘流浪漢’,他們衣衫襤褸,食不果腹,但常常手里拿著書邊走邊讀。有一次,大約十年前吧,在美國,我甚至與這樣一位流浪漢攀談起來。他告訴我說,他正在‘實踐’一種哲學,他覺得很幸福。在西方人里面,哈耶克走得非常遠,他在<自由憲章>里曾經寫道:“自由并不意味著幸福。”他在這里直接使用了‘happiness’而不是‘快樂(pleasure)’。這就生出了把‘自由’與‘幸福’對立起來的意思。 對一個典型的中國人來說,把‘自由’與‘幸福’或者把‘自由’與‘快樂’如此尖銳地對立起來,是很難想象的。我在‘北大荒’結識過許多‘氓流’(真正自由得一無所有的流浪漢)。他們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自由的,他們也不會認為自由等同于幸福。他們最希望的,是有一個‘戶口’,有一個工作‘單位’,以及有一個‘家’,和與‘家’連接在一起的全部‘生活’。這也是一種‘幸福’觀念,這是一種必須依賴于物質生活的幸福。諾茲克是哈佛大學的哲學家,和羅爾斯一樣,是目前領先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最近的一本‘談心式’著作( 在經驗主義(例如洛克哲學)看來,一個人,他關于幸福的感覺必定取決于他有什么樣的欲望和這些欲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滿足。不過我們難免會問:豬和三葉蟲是幸福的嗎?如果中國人原本沒有多少欲望,他們樸素的田園生活是幸福的嗎?林語堂說過中國人有極強的生存本能和適應環境的能力。在他看來,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正是中國傳統意識中最幸福并且也是自由的生活。 老資格的法學和道德哲學家費因伯格(J. Feinberg)批評過艾薩雅.伯林的“關于自由的兩個概念”(一篇政治哲學名作,其漢語譯文1996年發表在<公共論叢>第一輯上)。他的批評是基于他關于‘欲望’以及對欲望的‘限制’的討論上的。例如當我很窮,沒有錢買一輛‘卡迪拉克’豪華汽車時,從一個方面看,我缺少了‘積極自由(free to)’,因為我的欲望沒有得到滿足。從另一各方面看,難道不正是外在的‘貨幣’的制約迫使我克制我的欲望嗎?所以我在缺少了‘積極自由’的同時,也缺少了‘消極自由(free from)’。極而言之,一個完全沒有欲望的人,對施加給他的無論多么可怕的限制,總不會有什么失去‘消極自由’的感覺。因為他的‘自我’已經縮小成為一個沒有外延的‘點’,還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同時,我們也不能認為他享有任何程度的‘積極自由’,因為他完全沒有被欲望所驅動著的行動意志。所以,在費因伯格看來,消極和積極的自由只不過是欲望及其制約之間的各種關系的不同側面,它們在邏輯上是共生的。 憑心而論,費因伯格對伯林的批評有點兒不著邊際。不過他的批評涉及到了‘自由’與‘欲望’的關系。讓我們可以深究下去,把上面講的關于蘇格拉底,豬,和三葉蟲那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意識流’語言整理得比較清楚些。我還是把這個工作留給愿意深入思考的讀者去做吧(不妨再參考一下我在<公共論叢>1996年和1997年連載的那三篇文章)。 人是什么?人是介于神和獸之間的生物。人身上的神性就表現在他總是企圖超越他身上的獸性。梁漱溟說:人禽之辨,對后者而言是‘心為形役’,對前者而言則是‘形為心役’。我們的心靈總是掙扎著向上要擺脫物質世界對我們形體的束縛。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心靈停止了掙扎(也許是徹底為獸性所征服,也許是徹底超越了獸性),我們作為‘人’的存在方式也就隨之消失了。這個‘超越方式’的問題是個很重大的人生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人生的主題。物質世界對我們形體的束縛,在哲學上叫做‘因果律’或者‘必然’。例如我受物理規律的決定而感到饑餓并由此而生出種種‘食’的欲望,又由此而發生對物和財的追求。在康德的道德哲學里,為了避免道德主體由‘因果律’所產生的‘推托責任’的理由,干脆假設人的意志是不受任何物質條件束縛的‘自由意志’。在普遍主義原則下,從充分理性的自由意志就可以導出康德的‘道德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由于在現實中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由意志’,康德的道德哲學被認為帶有烏托邦色彩。不過,任何從現實世界的約束中試圖推導出康德的普遍主義道德律令的哲學努力,都無法回避康德面對的這個‘必然與自由’的兩難。 ‘自由’,于是可以理解為心靈對‘必然’的超越。既是‘必然的’,就必定是現實的,物質世界的,因果律的。因此,我們得到關于‘自由’的第一個也是最容易被人們忽略的界說:自由從來就是對具體現實而言的自由。 我想象著我在沙漠中爬行,渴求一片綠洲。炎炎烈日之下,我,或者我的心靈能夠想象的自由,不過是對‘一杯水的欲望’的超越。我是一個中國人,我不是基督,不能想象我正在經歷上帝的考驗,也不能想象天國里的無限自由。我要求的自由總是有限的卻是離我最近的自由,那是由于我不得不首先關心我在此世的生存。 但是,難道‘自由’就僅僅是追求一個比‘現實’稍高的目標嗎?對古典自由主義者來說,確實如此。自由首先應當是身體的活動自由,是個體生命能夠延續的自由。其次,自由是指個體生命得以發展的必要條件的滿足。例如必要的財產權利給個體提供了展開物質活動的手段,必要的政治權利給個體提供了保護和擴展個體的其它權利的手段。因此,對古典自由主義而言,自由是被具體權利界定了的具體的自由,是有限的自由,是關于自由的權利。個體的權利,主要地或者全部地依賴于其他個體對該權利的承認。我對我的生命和財產的權利,同時就是別人必須承擔的不來侵犯我的生命和財產的義務。因此個體之間相互尊重生命和財產權利,成為每一個個體的自由的保障,也叫做文明社會的‘道德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古典自由主義所追求的自由又大大超越了對‘比現實稍高的目標’的追求。因為這種古典意義的自由要求實現康德的“以每一個個體為目的的道德王國”。這就回到文章開始提到的霍布斯的‘自由’概念。叢林里孤獨的一只野獸的‘自由’,對古典自由主義來說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為這野獸的生命隨時可能遭到其它獸類的侵襲,它的各種‘權利’完全沒有得到其它個體的尊重,它只不過是其它個體追求其它個體自身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這樣我們得到關于‘自由’的第二個界說:在任何群體中,個體的自由只能通過個體之間的倫理關系來實現。 ‘權利’,‘義務’,‘自由’和‘道德’,在西方社會里當然有它們自己的發生學淵源。我們在中國社會和漢語詞匯里也許找不到非常適當的對應概念;最基本的概念都是‘不可翻譯’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社會里沒有‘自由’,‘權利’,‘義務’等等概念所反映的生存困境。自由是對必然的超越,這在任何社會里對任何個人都是正確的,因為每一個人都體驗過并且仍然體驗著心靈對現世束縛的掙扎。我們心靈的向上的努力,不斷對我們提出改進生存條件的要求。這就是‘文明化’過程,用古典哲學的眼光來看,也就是“人從必然向著自由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從現代哲學的角度來看,就是每一個人從他所處的特殊環境中體驗和理解他的生命意義的過程。在每一個特殊環境里,‘權利’,‘義務’,‘自由’和‘道德’于是都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歷史或發生學淵源。 中國正在試圖進入一個市場社會。但是中國的市場社會注定了要在中西文明的不斷沖撞中誕生。以往的一百多年歷史,是鄉土中國在西方人堅船利炮的轟擊下不得不實行工業化并且進一步追求現代化的歷史.在這段歷史時期的絕大多數年代里,從危難中拯救‘民族’以及伴隨著而來的民族認同,掩蓋了隨工業化及專業分工而來的‘個人’訴求。只是到了本世紀八十年代的后期,對多數中國人而言,‘救亡’和‘溫飽’問題終于不再成為‘問題’。于是,中國人的心靈在這個已經‘西化’了的世界里感受到‘失落’。于是,西方人苦苦糾纏于其中的‘現代性問題’也成了糾纏著我們中國人的問題。發端于啟蒙時期的西方人的‘現代性問題’,不論在德克海姆,黑格爾,和韋伯那里,還是在福柯,哈貝瑪斯,和麥肯塔爾那里,總可以歸結為“自由與制度的相互依賴與沖突”---所謂自由與制度之間的緊張。 我在<讀書>最近的幾期里談到了自由與制度之間的緊張關系,以及‘現代性問題’。在這里我想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中國人不能在中國傳統中仔細想清楚‘自由’的涵義,那就不可能成功地處理自由與制度的緊張。這話當然也適用于西方人。我知道,德國人對自由的理解就很不同于美國人,而美國人也不同于法國人。我還知道,即便是同一個國家里的人,個人歷史的不同決定了人們對自由的理解的不同。所以,對自由與制度之間的緊張關系的感受,根本上是每一個個人自己的事情。但是每一個人,當他想要處理這種緊張關系時,例如試圖去改變現存制度安排時,他馬上發現面臨著的是一個倫理問題。我反復地,在不同深度上寫過市場經濟和市場社會的道德基礎問題。我覺得我們現代中國人都被這一百多年以來的發展拋入了一個‘陌生’的世界。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基礎已經瓦解了,而西方社會的倫理基礎又不可能被當成中國人社會交往的前提。于是道德哲學的重建就成了當務之急。我之所以要談‘自由’,也是因為自由是道德哲學的一個話題。而我之所以要和青年朋友談這個話題,是因為我不認為我能夠在未來的十年內找到一個新的道德哲學。道德哲學將是下一個世紀中國人不得不面對的重大課題。現在的青年人將不得不在自己成熟的中年,反復思考這個問題并且苦苦糾纏于這個既是私人生活中的也是公共大眾的問題。青年人,我祝你幸福,注你找到自由,也注你走運。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觀點分析 > 汪丁丁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