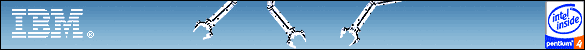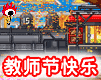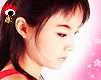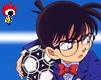| 北海三劍客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9月06日 22:03 《新遠見》雜志 | ||||||||||
|
三個人里,我們只見到了王飛欣。任玉嶺恰好出差在外,他一直工作很忙。劉克府我們不敢驚擾,他現在身體太弱。想當初,一個是研究體制改革的專家,他出了一個想法;一個是風華正茂的副市長,他接受了一個想法;一個是吃螃蟹的企業家,他實踐著一個想法。三個人恰好代表了產、官、研。研者巧思多智、灑脫超凡;官者熱情奔放、魅力脫俗;產者勤奮刻苦、堅忍不拔。三人攜手闖天涯,造就了一段江湖傳奇。
而今,研者嘴上超脫,心里其實依然火熱;官者說東道西,國事在心依然沉重;產者傷病纏身,往事揮之依然不去。 他們都老了,人老了就會陷入回憶。 他們都還年輕,年輕人對什么都不服氣。在中國二十余載改革開放歷程中,幾乎每一步都是“三劍客”們攜手闖蕩而來的,而中國未來的發展之路,依然少不了“三劍客”揮劍江湖。 我們應該記住他們,并且試著理解他們。 劍客之一:任玉嶺 差一步見到的精神領袖 差一步,就差一步啊!當本刊終于請到北海當年最核心的幾位歷史人物參加沙龍時,任玉嶺出差了。 任玉嶺,1960年南開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后在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委等部門工作,曾任廣西北海市副市長,現任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研究員職稱,四所大學的兼職教授。 總的來說,即使抹去北海那段歷史,如今的任玉嶺依然是一位相當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一位對社會焦點問題不吝熱情發表看法的學者,談反腐,談創業板,談西部開發,除了北海,似乎什么都是他的題目。在百度搜索他的名字,會有一連串的消息彈出。 一位當年在北海練過攤的人評價說,此人口才極佳,絕非等閑之輩,要不然怎么能當國務院參事?此言非虛。 幾乎每一個早期設計、參與北海開發的風云人物,都會推崇地稱他為“精神領袖”。 究竟什么樣的人才可以是精神領袖? 一癡 在任玉嶺眼里,90年代初的北海是未被驚擾的最后一塊世外桃源,惟一的缺點只是貧窮。這里三面環海,有世所僅見的白色沙灘,有安靜的深水良港,有豐富的海洋資源,有島,有山,有美人魚,有紅樹林。這一切使得原本在北京有自己事業的他堅持舉家遷來,而實際上,他這個副市長只是支援地方建設的掛職,而妻子在北京也有出色的事業。 “我后半輩子就放在北海了。”他曾經這樣說過。 改變北海面貌的心愿使他滿腔熱情地投入到推銷北海的行動中。當時北海已經被列入沿海14個開放城市之列,據說只要任玉嶺一見到內地企業家或外商,不管是否相識,肯定會極力推薦北海的好。凡是他認為有可能向北海投資的地方政府和企業,他都會傾力邀請。 據王飛欣介紹,最夸張的是一次國外招商活動,因為連續幾天不休息,剛從發言席上走下來的任玉嶺竟然累得休克。 任當年的助手楊建平說,他會在南寧到北京的火車上情不自禁地操起話筒,向旅客介紹北海,仿佛那些驚訝的旅客中間,肯定會有像他一樣熱愛那片土地的投資者。 北海開發建設的最初想法是在一次歷史性的聊天中形成的。王飛欣開玩笑說,不是這次聊天具有歷史性,而是任市長接見他們具有歷史性。因偶然機會到北海考察的王飛欣,碰到了正在北海考察的另一位早期參與者馬小林,任玉嶺恰好作陪。任玉嶺跟他們聊天,說你是北京來的,是搞研究的,能不能給北海出出主意?三個人一起神侃到很晚,王、馬兩人都回賓館睡覺了。 沒想到的是,任玉嶺居然根據他們聊天的內容,連夜開工,搞了一個方案出來。第二天一早,王、馬二人還沒起床,他就去敲門,把王飛欣、馬小林給感動壞了,就在喝早茶的時候簽了一個備忘錄。那可是代表市政府簽的,據說還把飯桌并起來,找了幾面小旗插上。 簽完字,任玉嶺就把這個備忘錄放到市委書記的桌子上,說你同意不同意吧,反正我已經簽了,先斬后奏。書記一看之下,就有了“事關重大,宜抓緊抓緊再抓緊”這個著名的批示。 三虎 做出這個批示的是王慶錄,當時的北海市委書記。一位知情人評價說,王書記素質很高,很有水平,任職很多年了,可是基于各種條件的限制,北海老是發展不起來,遠遠落后于其他13個開放城市,他心里著急,很想干出點事情來。也就是說,熱情很高,魄力很大。 任玉嶺敢想,王書記敢批,還要有人敢干。這個人就是當時的北海市長帥立國。 帥立國,桂林人,書香門第出身,藝術世家的背景給了他特殊的性格,據說字畫俱佳,尤其喜歡潑墨。任玉嶺的助手楊建平向我們介紹,帥市長生得一表人材,很受老百姓歡迎。十年后我們在北海采訪,幾乎每一位當事人都會敬佩地提到他。 帥立國屬虎,河北人王慶錄也屬虎,巧合的是,北京人任玉嶺居然也屬虎。三個外地人在政府層面拉開了北海熱潮的序幕。 所以,當時他們在那片江湖上有一個綽號:北海三虎。 盡管后來王慶錄出了問題,帥立國與黨委班子發生矛盾,本來就不太被當地官員圈子所容納的掛職干部任玉嶺黯然離職,但所有知情人都對他們那一屆政府的領導水平和為人贊譽有加,尤其與企業的關系以及對待各方面人士的開放和平等,均有馮小舟所謂的“要變天”的理想氣氛。 任玉嶺在北海市民中的形象尤其值得一提。楊建平說,他演講非常有渲染力,數據記得非常準確,他一講話,北海市民都聽。但他在經濟大潮里沒有沾手,自己沒有搞開發區。他一直是副市長,而且是主管科技的副市長。 十年一晃而過。如今,作為歷史人物的帥立國在潛心寫作回憶錄,當年對北海癡迷的任玉嶺對國家的事情“還是那樣認真”。 而王飛欣,作為一位體制改革的研究者,仍然超脫地做他應該做的事情,并且做到他應該做到的程度就適可而止,就像他當年與北海的若即若離一樣。 但王飛欣對任玉嶺的評價就沒有那樣超然物外。他說,任玉嶺對北海的感情是每一個北海市民心里的碑石,很少有人知道他離開的腳步有多么沉重。每當思緒及此,他都會為老朋友的當年際遇傷心落淚。 沒有人知道任玉嶺是否曾為北海淚流滿面。謹將詩人艾青的一句話送給他: 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劍客之二:王飛欣 理論制造商 很超脫地活著 “剛開始說辦開發區的時候征求農民意見,生產隊長剛從地里回來,挽著褲腿蹲在那兒。我說你們不用擔心,根據經驗,你們雖然是把土地轉讓出來了,但是最先富起來的一定是你們。這話說了還不到半年,我再見那位生產隊長時,已經是在開發區的開工典禮上。他坐著凌志小轎車,穿著西服,代表生產隊講話。現代化的東西他還不太適應,話筒不太會拿。” 王飛欣永遠記得1992年,北海的世界變化有多快。生產隊長的戲劇性變化是他親眼所見,而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他一手促成的。 因為,他正是用理論引爆北海的人。 宏大中把握北海脈絡 那段時間,中國社會處在一個大變動時期,在北京研究體制改革的學者王飛欣敏銳地感覺到了那種萌動。一批人已經下海,人員開始流動,有人開始發財,農民開始往城市里擠。 到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人們又一次感覺到了思想上的解放。一個老人在南方畫了一個圈,于是很多學校、機關、國營單位的人想下海。 經過一些改革后,民間畢竟有些活力,所謂的體外循環資金已經占據比較大的位置。有些地區發展很快,比如深圳,資源開始流動,孔雀東南飛,人才流向沿海,因為那邊工資高,也比較靈活。 王飛欣在新疆看到了一種困境:人才留不住。他建議,是不是可以學一下沿海?人家高薪,你也活一點。但新疆方面的人說,高薪政策不是我們說了算,國家管理體制、財政制度都約束得很緊。即使提高了一些工資,也不可能做得面面俱到,就會引起變動,招來女婿氣走兒。 王飛欣想,為什么不到沿海建一個經濟特區呢? 這個地方就是北海。因為當時說,那里是大西南出海口。 理論生產在那個年代 當時在國家體改委任職的王飛欣,到海南參加一個金融體制改革研討會,會后坐船到北海考察。在14個沿海開放城市里,這是最落后、規模最小、最不知名的一個。16萬人口,沒有幾家外資企業,有那么幾家還是假洋鬼子,出口轉內銷的。 成片開發當時是讓外國人做,一個天津,一個是海南楊浦。既然讓外國人成片開發,為什么不讓中國人成片開發?中國內地有這個需求,北海自己又開發不起來,為什么不讓內地的省份來開發呢? 王飛欣總結說,這就是要素市場存在的需求。 1992年,土地要素市場開發的代表是北海,資本市場的代表是深圳、上海,中國的改革從此走上了不歸路,不可能再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了。 王飛欣發現,地方政府最撓頭的就是改變城市的錢從哪兒來?他說,錢就在你們腳下。 面對這種想法,當時北海市領導曾經謹慎地與他討論,搞這么一個大膽的方案會不會犯錯誤?王飛欣說,放心,第一不會違法,第二沒有大的違規,第三就是有小的違規,也一定符合改革發展方向。 三句話穩住了北海市政府領導忐忑的心。 按照深圳和海南的經驗,剛開始都是內聯體制,靠內地開發基礎條件,所以應該先內聯。靠什么吸引內聯?就是靠要素市場。 無人問津的一個小城市,忽然全國矚目。 王飛欣說,改革不見得都有好下場,很可能就是犧牲品。北海就是犧牲品,變成了一個泡沫經濟的博物館。 他為北海感到委屈。當時已經有多個項目在市政府,上億美元的項目也正在立項過程中,很多國內外大企業都要投資,誰料想一下子被截斷了。 開發區心里著急,當時在開發區管委會掛職的他體會深刻。明明不具備開工條件,市政府逼著開工。為什么?因為自治區政府說,光看你們炒地,沒見你們開工。區政府有這個說法,那么全國呢?中央呢?從1992年起,中央就不斷派工作組到北海調查。自治區有壓力,北海市政府也有壓力。但是,明明連土地勘測都沒有搞完,規劃都沒有做出來,開什么工呢?那個生產隊長就是參加那樣的開工典禮來的,典禮之后馬上收工,就是弄一個儀式,要不然不好交待。 市政府當時給了王飛欣一個助理頭銜,但實際上他沒有做那個工作。1993年10月,這個超脫的經濟學者回到了北京。 他終究是搞改革理論研究的人,知道自己這個身份應該做到什么程度。他沒有去公司,因為公務員是不能辦公司的,即使大家紛紛去辦。他在鄉鎮企業城里沒有任何職務,也沒有任何股權。作為開發區管委會主任,他只做服務。 回京后體改委把他轉到體改研究會當副秘書長,王飛欣自己才辦了一個咨詢中心,同時組建了一個公司,任公司的老總。 王飛欣說,他不想寫關于北海的文字。因為,“客觀地寫沒地方發表,不客觀地寫則是違心。” 劍客之三:劉克府 我們不敢采訪的人 1993年4月28日,劉克府感覺自己開始崩潰。 這一天在北海編年史里是沉沒的開始。那一天他起床洗臉,抖擻精神準備像往常一樣開始忙碌的工作。當他走出北海最負盛名的皇都大廈的辦公室,突然發現,樓道里沒人,電梯里沒人,大堂里也沒人,似乎整個城市都空了。 太陽炎熱而寂寞地照著,但北海的冬天已經來臨。 不知所措,頭皮發麻,他病倒了:渾身所有關節都從里向外疼,胃出血導致9個月低燒,那樣虛弱,以至于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 在北海創業的知情人士說,劉克府是一個心重的人。他太在乎,他已經為北海提前透支了太多生命的精華。 我們此次沒有當面采訪劉克府,因為他的朋友說:“他的身體狀況不能再受刺激了。”我們對他的描述都是道聽途說而來。 我們不敢用北海刺激他。 至今身體還很虛弱的他,是北海鄉鎮企業城的創建者之一。 城夢 1991年底的某一天,劉克府聽從朋友意見,第一次來到北海,發現這里的海鮮真是便宜! 劉克府不是一驚一咋的窮人,當年他任常務副總的那家公司在北京跺地有聲。但由于政府官員之間對企業發展的意見不一,導致公司被撤并。他本來可以按照慣例獲得一個至少相同級別的位置,然后在仕途發展。但他選擇了下海,選擇了北海。 全市20萬人,一年1.6億的財政收入,這就是當年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的北海。 劉克府知道它有絕美的沙灘、深水的良港,他也清楚當時對大西南出海口的討論中,北海是焦點之一。這一切讓他想到了兩個字:城市。 作為老革命的后代,自小被寄養在河北山區,他在內心深處對城市有一種強烈的向往。盡管已經是城里人了,但他對農村與農民的生活體驗切身。他相信徹底改變農村狀況的途徑就是把農村變成城市。農村,北海,改變,城市,漸漸的,這些意象在他腦海里建立起了聯系。 他對這一想法的信心,部分來自于當年火熱的義烏改革。城市化終究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發展鄉鎮企業是走向這條路的時代班車。看著中國地圖,劉克府覺得應該有越來越多的新興城市涌起。他真誠地信仰這一點,面對北海,一種宏大的歷史使命感在內心升起。在一張白紙上描繪歷史,這一理想的激動驅使已近50歲的他毅然走了過去。 迷夢 開發北海的具體想法,是劉克府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與北海市相關部門領導在“浪漫境界般的”頭腦風暴中形成的。這些人中間,應該有王飛欣,有任玉嶺,有帥立國,有王慶錄。 如何為北海改天換地?當地豐富的土地資源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此后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把土地化片成區,成立開發區。由企業運作開發區的土地,這些企業獲得開發區內土地的“招商權”而不是使用權,避開了國家對土地一次性規劃的數量限制。而以商招商的模式也最大限度地刺激了最先到達北海的大企業。 劉克府出手了鄉鎮企業城的第一塊土地,但別人對這塊土地的處理卻讓他驚訝得一時沒有反應過來:3.5萬一畝的價格出手,本來是基于起步的考慮。但那位聰明的海南炒家,自己的錢幾乎沒動,只交了一點定金,轉手就以5萬元一畝的價格賣給了下家,還輕松地說,反正下家要出錢,余款就由下家直接交給鄉鎮企業城吧。 北海炒地的浪潮就這樣從第一筆交易就開始了。 以后的故事簡直就是財富神話。全國各地的炒家,連同整箱整箱的現金,向北海蜂擁而來,一塊土地幾個小時就換一個主人。某人來的時候揣了100萬,回去的時候已經多了一個零,這樣的傳說不脛而走。最高檔的皇都大廈和富麗華大廈的大堂已經成了土地交易市場,熙熙攘攘,人流如潮。蹬三輪的師傅都會問你:手里有地,要嗎? 大家在有意識地炒地,大家也在無意識地集體瘋狂。而作為鄉鎮企業城的老總之一,劉克府從來沒在夜里三點鐘之前睡過覺,往往會在晚上12點開第一個會,凌晨2點開第二個。年近50的他像年輕人一樣始終處在無法言狀的亢奮中,可以一天不進滴水粒米。 隨著財富的洶涌聚集,他們開始著手更長遠的計劃。1992年不到10個月,北海就集資66億,到1993年4月底,達到120個億,相當于深圳最早三年集資的兩倍還多。公路建造開始了,120米寬的主干道,是未來北海這樣一個“中國的新加坡”所需要的。教育設施不可或缺,召集內地高水平的教師,建了一所現代化寄宿學校。還有高檔書店,時裝表演…… 眼看著,一個遠超深圳的新城就要誕生。 殘夢 這樣一個大浪的形成,也有當時北海市政府推波助瀾的功勞。僅僅幾個月就批劃十幾個開發區,土地越來越多,價格一路飆升,從3萬到30萬,再到80萬。大批大批的土地被鐵絲網圈了起來,荒草還沒有長高,卻已經幾易主人。 讓人熱血上涌的利潤和日漸稀少的資源終于滋生了腐敗。據說,當年土地局的地圖里赫然標著某某的土地。 此時,稍微清醒的人建議政府建立土地期貨市場以規避風險,但政府已經沒有這個心思,其實也沒有能力控制了。 就像劉克府數年后的總結:“土地市場化真不是簡單的事情。” 一塊塊荒草隨風搖曳的土地寂靜地圍在鐵絲網里,海風在黑洞洞的半截別墅中穿堂而過。街道空了,歌舞停了,炒地賺了錢的一去不返,真正想搞建設的卻被深深套牢。 劉克府堅持認為,如果再有半年,北海就能走上良性循環,在他們規劃好的城市化大路上前進下去。 所以他不甘心,他在等,一直等到現在。 城市化以及在北海創造歷史的恢宏設想曾經是劉克府后半生的一個夢。幾年后的一次老朋友聚會上,他唱起慷慨激昂的蘇聯歌曲,禁不住淚流滿面。 他已經老了。在正統教育的背景里長大,卻實在不懂市場經濟。劉克府們已經算是同齡人中腦筋靈活的,但與年輕一代相比,還是慢了半拍。 在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里,他做了一個并不圓滿的夢。生活還算精彩,角色還算正面。他說,可以無悔了。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財富人物 > 《新遠見》2004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