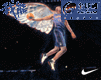| “逃離”商業 三個地產商人的藝術夢想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12日 17:30 中國企業家 | ||||||||||
|
在殘酷、利益至上的商業競爭中,他們都保持著對藝術的高度熱情,有的人甚至認為那是自己的最后歸宿 文/本刊記者 劉建強 現在可以跟中國的企業家們談點兒商業之外的事情,比如藝術。20多年過去了,中
比如收藏。大連萬達集團迄今在中國近現代書畫作品收藏上已投入逾億元,藏品以齊白石、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鴻、吳冠中等大師的作品為主。2004年6月至7月,萬達集團攜所藏吳冠中畫作分別在巴黎和北京巡展,引起轟動。據悉,萬達集團將在北京或上海為其藏品建造一座美術館。 河南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也收藏了大量繪畫書法作品。他的辦公室里,掛著一幅巨大的陳逸飛的人物油畫。 在北京,今典集團已經建成了自己的美術館,而且是國內最大的私立美術館。今典集團董事長張寶全從小畫畫,并曾涉足寫作、導演等藝術領域。“藝術才是我的主業。”張寶全說。 這樣的說法還可以在依蓮軒地產公司總經理劉博、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那里聽到。這兩位是詩人。 正如你所發現的,這些企業家都是地產開發商。必須說明,這是一個巧合。當我們追問為什么房地產行業會出現這么多從事過藝術創作的人時,來自采訪對象的回答都是:其實并不多。 或者,建筑本身的藝術特性更容易吸引有藝術氣質的人。劉博、黃怒波、張寶全,這三位蓋的房子各具特色,按劉博的話說:詩人(藝術家)做出來的東西必然是另類的。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個流浪詩人。”黃怒波說。 “寫詩使我變得嬌柔,嬌柔得更像一個女人。”在一本詩歌小冊子里,劉博這樣寫道。 在殘酷、利益至上的商業競爭中,他們都保持著對藝術的高度熱情,有的甚至認為那是自己的最后歸宿。“逃離”商業,與商業保持一定的距離,使這些商人與他們的同行區別開來。 “我們不是主流。”這個否定句讓他們自豪。 不能要求每個企業家都對藝術感興趣。但是,在普通人眼里,有了這些“藝術商人”,商業就變得好看起來。 黃怒波:詩歌讓我內心的善良沒有丟掉 在第二屆“中國企業家領袖年會”上,黃怒波自我介紹說“我是一個詩人”,引來大家一陣哄笑。 “明年會出兩本詩集,一本寫帕米爾高原,一本寫黃山宏村,后年創作長詩《綠度母》。” 一個地產商人的腦袋里同時裝著商業計劃和寫作計劃,黃怒波自己也“感到奇怪”:“有時候我早上6點鐘起來寫詩,然后司機來接我上班,我會在車里接著寫。但是一進辦公室,詩就忘了,開始想工作。” 黃怒波與人們印象中的詩人形象相差很大—身高一米九,更像一個籃球運動員。13歲,黃怒波在《寧夏日報》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詩歌,這或許是他沒有投奔籃球的動力所在。 插隊的時候,黃閱讀了“除《金瓶梅》、《紅與黑》外能借到的所有文學名著”,這使得后來他在北大中文系讀書時候“毫不費力”。那時候,他的夢想是出自己的詩集。現在,一本精裝的《落英集》就擺在他的桌子上。黃不避諱詩集出版是自己花的錢:“我做企業就是為了詩。詩歌才是我的職業。” 一個詩人怎么做企業?而且是一個大企業?“企業首先要合法,但不一定講良心。詩歌講的是良心。詩人做企業,要考慮法律之外的東西,不能只顧自己的利益,把對方置于死地。我做企業沒坑過誰。一個心靈骯臟的人寫不了很美很傷感的詩,他會寫得很假。真正敢于解剖自己心靈的人,一定是單純的,盡管他有這樣那樣的弱點。”黃說,當拆遷居民提出更高的補償要求時,他總是盡可能地答應,比如大鐘寺商業廣場項目,“與當地農民談到了四六分成,其實完全可以談到二點幾。”黃認為,是詩歌讓他沒有丟掉內心的善良:“讓我沒有變質。地是人家的命根子,我們什么也沒有,憑著比人家知識多、資源廣就能賺錢,不能賺得太黑了。” 在另一個項目合同已簽訂的情況下,對方反悔了,要求再加5000萬元。黃怒波與他們“喝了一頓酒”,成了朋友,5000萬就給了對方。 但是對于某些依仗各種勢力的人,黃自稱“詩人本性”讓他永不低頭:“狹路相逢勇者勝。當初我就什么都沒有,怕什么?” 黃怒波認為,這種“詩人脾氣”反而給他帶來了更多的商業機會。他的項目有不少是當地政府慕名找上門來,他很喜歡別人對他的評價:“怒波是個男子漢。”但是他又反對冒險:“沒有把握的事情不做,對做‘最大’、‘教父’沒興趣。” 黃怒波早期的詩歌文字淺顯,講究韻律,很像一首首上口的流行歌曲的歌詞。在最近要出版的《城市流浪集》里,黃的風格大變。帶著濃重的西北口音,黃怒波在位于遠洋大廈的辦公室里朗誦他的新詩:晨/將像馬的屁股/又被抽打/街/被骯臟過/又被骯臟…… 他認真地問道:“誰謀殺了雪/讓我的街巷總是骯臟?” 黃怒波說,如果不是做房地產,他對城市認識不了這么深刻。在他眼里,城市是理性的,但不是人性的。現在,他認為詩歌的作用就是批判,對于他,就是要批判他生活的城市,“物欲越強越需要批判”,“這本詩集里全是對城市的無奈和反抗。” “一個人下海這么多年,處在忙碌的商業環境中,還能堅持寫詩,這本身就很不容易。”劉博這么評價黃怒波。 黃不愿意讓人把自己歸類于財富階層:“我對這個階層毫無興趣。我只是一個過客。很多人有錢,但是沒有靈魂。”因此,大多時候,黃都是獨來獨往,尤其是做項目,“決不跟人合作”—他不愿意為了掙錢跟別人商量來商量去。在偶爾推脫不掉的企業家聚會中,黃的內心總是感到“孤獨”。 近年來,黃怒波為各類詩歌活動捐資近千萬元:“中坤集團有個設想—通過企業來推動中國詩歌的復興。”他說,拿出幾千萬來發展詩歌,要比買個豪宅有價值吧。因此,在很多人眼里,黃怒波是作為詩歌活動家、資助者出現的。 “商業不是我的興趣所在。過幾年,我的團隊建設好了,我就會退出,去過真正的詩人生活。” 劉博:寫詩讓我放松 劉博跟黃怒波只有一面之交。今年3月21日“國際詩歌節”,劉博的“格調”樓盤開盤,同時在售樓處舉行了大型詩歌朗誦會。那天,她第一次聽說京城還有一個寫詩的地產商,叫黃怒波。不久,在北大詩歌研究中心(由黃怒波長期資助)成立當天,她見到了黃。 在那次詩歌朗誦會上,劉博在臺上喊道:“為了我們詩人還活著歡呼吧。”臺下的著名、非著名的詩人們響應如潮。但,這是一個地產商賣房子時應該說的話嗎? “藝術家做的東西肯定不是面對大眾的,只是迎合了一小部分人的需求,我覺得這就夠了。比如畢加索的畫,并不是每個人都欣賞,但是能賣出那么高的價錢來。”劉博說。 畢加索的畫很少有畫家買得起,劉博的“人文地產”代表作“格調”也很少有詩人買得起。“我們提倡的是詩歌精神。事實上,在很多人身上都可以激發出這種精神來。并不一定要把房子賣給詩人,我們是想藉此表達出對詩歌的尊重。” “格調”的售樓處是一座高大的廠房式的建筑,完全由鋼鐵構成,這是她與設計師共同討論的結果。劉博說,詩人經商首先考慮的問題不是能賺多少錢,而是能不能把它做得漂亮。她承認這可能會使自己不完全按照市場的規律去辦事,但是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就是沒有條條框框,做得好的話,“確實能帶來出乎意料的效益。” 上個世紀80年代,劉博在河南省作協的一份刊物作編輯,同時寫詩、畫油畫。當時她的夢想是當個作家。之后,她進入亞細亞集團,擔任公關部主任,然后到海南拓展亞細亞的業務。在那個淘金時代,她以傳奇般的速度擁有了豪華別墅和轎車。“那是1992年啊。”劉博說。這段經歷讓她感覺很愜意。那時候,物質與精神交鋒激烈,劉博說她從未有過心靈的掙扎:“我沒有想過做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詩人。商業本身是很干凈的,雖然有不擇手段的商人,但更多的還是憑自己的智慧和實力贏得商業機會。” 1994年,當股票變成廢紙(沒能上市),地產又被套牢后,劉博表現出了一個詩人的灑脫:一無所有地來到北京,在一間簡陋的出租屋住下來。“很多朋友都奇怪劉博都這樣了怎么還能成天很快樂。我覺得世界很小,心的領域很大,詩人的思想比較純凈,心里很多東西都是過濾過的。” 劉博同意黃怒波的觀點:詩人是憑良心做事的。“對于人和事,我很少用數字來衡量,完全憑良心。問題越是復雜,我越不用商人的邏輯去對待它。事實上,很多時候是你把問題想復雜了。”成為依蓮軒地產公司董事總經理之后,昔日的豪華生活再次來到身邊。“你進入這個行當,積累了一定的財富,然而,最能打動你的是什么呢?最后,物質生活還是會把你帶回精神的領地。”在劉博看來,賺錢的興奮沒有藝術帶給她的興奮長久。 與黃怒波不同,劉博喜歡聚會、朗誦,生活很豐富:“詩歌有詩歌的朋友,地產有地產的朋友,收藏有收藏的朋友。”她是詩歌組織“干草部落”的7位成員之一。這7位女性,來自各行各業,生活條件都很優裕。劉博說,“干草部落”的名氣很大,最遠到過臺灣去朗誦,是人家邀請去的。“我們就像是在‘走穴’。”劉博說。 劉博熱愛中式衣服和家具,衣服穿在身上,家具用來收藏。她并不在意自己從事的是不是主流商業。“我從來沒想過。”她也不愿意自費出版詩集,她希望自己將來要出的東西能夠影響別人。 “寫詩讓我放松。如果有一天不做這個職業了,我向往一種寫寫詩、畫畫畫兒的生活。我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享受藝術帶給人的清淡的生活。” “格調”售樓處里掛著兩個鳥籠子。詩人劉博忽略了小鳥的自由。 張寶全:藝術是逃離生活的手段 2003年,張寶全畫了大量的畫,還買了一把大提琴。“除了銅管,其他樂器我差不多都會,”張寶全說,“我天生有藝術情結。” 比起黃怒波和劉博來,張寶全在藝術上走得更遠。他寫過劇本、導演過電影,其書法作品曾參加全國聯展,畫作被有關機構收藏。 今日美術館偌大的空間讓張寶全感覺自在。通過一些較高水平的展覽,這個由地產商創建的美術館在美術界已經有了相當的名氣。張寶全的辦公室與今日美術館相隔不遠,里面有個不大的套間,是他的畫室。一面墻上貼滿張的行草作品,桌子上剛寫好的一張,內容來自《圣經》:身在曠野,我心飛揚。 “藝術是我超越或者逃離生活的手段。”張寶全說。作為“成功人士”,財富階層的一員,他真的有這種需要嗎?“財富只代表你對資本的控制力加強。作為有七情六欲的人,大家其實是沒有差別的。每個人的生活都像圍城,只是需要擺脫的東西不同。”張寶全說,作為藝術家,他能夠通過各種形式來“脫離”生活,這是比常人優越的地方。 當年,張寶全在深圳拍電視劇,一個做生意的朋友請他和一大群人吃飯、卡拉OK。他看到其中一位官員不顧妻子在身邊,邊唱歌邊與歌廳小姐糾纏不休,他的妻子只是沖別人做做鬼臉。“人們的精神、道德墮落到了那樣的地步。”當時張寶全一文不名,又礙著朋友,只能默默忍受。“人如果沒有心靈的自由,簡直糟糕透了。” 財富給張寶全帶來了他想要的自由。“當你在物質上獲得一定的成功,又不太愿意繼續出賣自己、把自己當成掙錢的工具的時候,你就能在不自由中部分地保持獨立。”但是他承認,他找不到年輕時候那種“非常寧靜”的創作狀態了。他很懷念以前那段人與人之間物質條件差別不大的時光,那時候,對藝術的追求“很純粹”。曾經像黃怒波和劉博一樣,張寶全認為自己的終極目標就是藝術,現在他放棄了這種想法:“這是不現實的。” 張寶全說,做地產能把他的素質充分發揮出來,“做地產我可以做到一流,專業從事藝術可能只是二流或者再好一點兒。用商人的思維構建商業模式,用藝術家的思維去設計,既能賺錢又能讓自己獲得精神上的平衡。”他認為,藝術家和商人的混合使他能夠成為這個行業中“獨特的風景”。“對于我,藝術和商業不能夠絕對分開。” 所以,他創建美術館,也是要贏利的,“否則我養不起。”在他的設想里,他將與全國各地的畫廊簽約,統一銷售書畫家們的作品—有了“今日美術館”這樣的品牌,名人就不會因為自己的作品在小地方出現而不快,小地方也能夠因此買到名人的作品。 比起去年,張寶全畫得比較少,字寫得比較多。盡管創作狀態不如年輕時“純粹”,但是他自認還是有了進步。“我創作的變化我自己知道。” 張寶全所謂的“藝術是我的主業”,并不是說他要成為一個職業藝術家。他盡可能地把藝術跟他從事的一切“混合”起來,使它們看上去超越了商業,而在暗地里,又讓它們與商業保持了親密的關系。張寶全把這叫做“假公(商業)濟私(藝術)”。 張的辦公室里也有兩只鳥籠,是打開的。兩只顏色不同的鳥在高大的房間里飛飛停停。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財富人物 > 《中國企業家》2004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