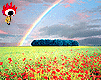我買《云麾將軍帖》的故事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9月24日 20:36 《藝術市場》 |
|
文/ 錢江 歲月的海灘上潮來潮去,待到生命之舟已經遠離岸邊,人才會發覺自己是多么地不足。就拿天天在用的漢字來說,無非由橫豎撇捺折點組成,要把它們安排得當就不容易,要組成個書法家的樣子就更難了。 我還是學過兩天寫字的,但是“文革”中上山下鄉、屯田邊疆的風沙吹折了我的學書經歷。那是荒唐歲月,本來已無話可說,誰知傳統文化自有錚錚傲骨,在塞上金灘走馬、彎腰脫坯兩年之后,我突然覺悟不應該把過去所學通通忘掉,就找支毛筆閑來涂上兩筆。父親知道了認真起來,來信說要學就要像個樣子,待探親時找位名家指點一下。 1973年探親回上海,熱心的葉崗叔叔(大畫家葉淺予之弟)帶我去見名畫家唐云。那時我在沙漠里種地久了,也不知唐云究竟是何人。葉崗叔叔說:“他是大藝術家,畫和字都好。” 當此之時,已不再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倒還是真的。待到了唐云家中,見是位胖乎乎的老先生,也不怕獻丑,徑直地把兩張紙遞了上去求教。其中一張紙上寫的是岳飛的《滿江紅》。 突聽得唐云帶著杭州音大聲說道:“這是趙字么!學趙僅得皮毛,則趙字如蛇啊,不易歸真。” 真是嚇了我一跳。原來“文革”之初,外祖父家碑帖散盡,我隨意抄了一本回家,竟是元初趙子昂的“蘭亭十三跋”,還有他臨摹的《蘭亭序》,是個很不錯的刻本。我照著寫字,沒想到就被“纏住”了。 那天的唐云說了些初學的年輕人不必先從學趙字開始的話,亦說我身居塞外,當聚豪放之氣。我向他討教可從何帖開始。唐云應聲說:“李邕《云麾將軍帖》。” 返塞路上途經北京,聽說琉璃廠商店經歷了“文革”掃蕩后重開,就去看個究竟。只見街上清清冷冷,我冒冒失失地一頭撞進榮寶齋對面的“慶云堂”。 這家碑帖商店里一個顧客也沒有,3位店員在柜臺后坐著,都不說話,店堂里鴉雀無聲。我怯生生問了一句:“李邕的《云麾將軍帖》有沒有?”“有。”一位年紀大的馬上起身入內堂,拿出兩本碑帖來。一本綠綾紙面的正是《云麾將軍帖》,打開一看,墨色沉著,拓工精細,看得出是一本好帖。 “多少錢?”我對碑帖的價格一點兒概念也沒有。 “四塊。”上年紀的店員又向我展示另一本:“故宮珂羅版印的《快雪時晴帖》,當年一共印了500本,現在五塊五。用不了十塊錢就一起拿走了。” 10塊!我的手插入口袋,那里一共只有26元錢,是探親后的全部貨幣財產。我還是一咬牙,把兩本帖都買了。要知道我當時一個月的“兵團”津貼不過7元錢。 買是買了,臨也臨過幾遍,終于沒有長久堅持,不過我寫的字里多少有了李北海的影子。 9年過去,我大學畢業后回到北京,第二次走進慶云堂。這時的店堂已經氣派些了,店里也有了顧客。我問:“有《云麾將軍帖》嗎?” “有。”又是應聲而答,一位中年人走進內堂,取出一本木制封面的《云麾將軍帖》拓本遞過來。封面比過去講究多了,翻開細看,拓本則未必精于我的。問一聲價錢,中年人回答:“460元。”我嚇了一跳,趕緊還了離去。過了好一會兒才回味過來,9年前自己在這里以9.5元錢作了一次正確的投資。只可惜當年阮囊羞澀,要不然多買幾本…… 我不敢想下去了。 時間又過了10來年,我于1994年到上海工作前第三次走進慶云堂,第三次詢問《云麾將軍帖》。這時,柜臺內站著的是一個年輕人,他回答:“這帖有。” “多少錢?” “打上火膝印了。” “什么意思?” “打了火漆印就是貴了唄!”他不客氣地告訴我。當年我曾在這里感受到的斯文書卷氣已經難以尋覓了。 低頭看看柜臺里,一些舊日碑帖,打了火膝印的,差不多在三千元左右。沒有發現《云麾將軍帖》,這回我判斷年輕的店員不會拿給我看了,于是就走了。 我的《云麾將軍帖》還在書柜里躺著。日積月累,如今我的碑帖已漸成規模,惟嘆學書少有長進。不過我確實由此打開了一片新的知識天地,至今還深深懷念唐云先生。而慶云堂的故事,即折射出我生命的軌跡,也通過市場價格映照出歷史的變化。 (作者 人民日報社) 責任編輯:吳京波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理財 > 收藏 > 收藏家 > 正文 |
|
| ||||
| 熱 點 專 題 | ||||
|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