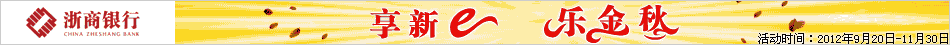周其仁:征地權是行政主導城鎮化一把利器
周其仁
征地權早就有。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百廢待興,鐵路先行。1950年6月政務院頒布的《鐵路留用土地辦法》,規定鐵路建設用地,可“由路局通過地方政府收買或征購之”。這里的“征購”,也要付價,但帶有某種強制性質。“征購”完畢的時候,土地所有權轉移到鐵路局,也就是轉為國有。
城市建設也有類似需要。也是1950年,政務院通過《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規定“國家為了市政建設需要及其他需要征用私人所有的農業土地時,須給予適當代價,或以相等之國有土地調換之。對于耕作該項土地的農民亦應給予適當的安置,并對其在該項土地上的生產投資(如鑿井、植樹等)及其他損失,應給予公平合理的補償”。這里的“征用”,也帶有國家強制的性質。
再過三年,經濟建設大規模展開,涉及到的土地不僅僅限于鐵路和市政,于是1953年政務院通過《關于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辦法》。這是第一個征地的專項行政法規,其中明確發生征地,“應該盡量用國有、公有土地調劑”,實在無法調劑的,“應該發給補償費或者補助費”,并規定了補償或補助的標準。
到1958年,上述征地辦法作了修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對“征地必須給予補償”的原則打了折扣:其一,“對于征用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土地,如果社員大會或者社員代表大會認為對社員生活沒有影響,不需要補償,經縣級政府同意,也可以不發給補償費”;其二,“征用農業生產合作社使用的非社員的土地,如果土地所有人不從事農業生產,又不以土地收入維持生活,可以不發補助費,但必須經本人同意”。這是1月6日全國人大通過的。等大躍進風暴一來,這兩大折扣究竟如何實施,是不是為當年的“共產風”提供了“法律根據”,要請歷史學家們去刨根究底了。
這套《辦法》一直用到1982年。是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則通過了《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列》,由國務院頒布實施。這部法例的總根據,是82憲法第10條的以下準則:“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據此,新《條例》規定了征地的適用范圍,申報、審批與執行程序,補償標準與安置辦法等,為新時期的征地行為提供了一個法律框架。
現在看,這套征地框架反映的是當時的觀念與現實,即農村和農民主要搞農業,而靠城鎮國有機構來發展工商服務各業。因此,1982年的《征地條例》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了“城鎮國有偏向”:第一,除了規定國家有權征用農村集體土地,再沒有給集體土地的其他轉讓方式留下合法空間,因為《征地條例》不但明令“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還規定“農村社隊不得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參與任何企業、事業的經營”。
第二,雖然給征地加上“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的限制條件,但含義模糊,更由于征地已構成土地轉用的惟一合法通道,所以也從根本上消除了“為商業利益”獲得土地的合法通道,導致所有土地開發,都要擠入“征地”框架才能進行。
第三,重申征地的強制性,“被征地社隊的干部和群眾應當服從國家需要,不得妨礙和阻撓”;并強調“征用的土地,所有權屬于國家”,也就是土地必須永久“變性”,完成國有化。其中,國有機構與農村社隊聯合投資建設的項目,凡使用農村集體土地的,也“視同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甚至“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進行建設或同農村社隊聯合投資建設的項目”,使用農村集體土地的,也可以“比照本條例的規定”辦成國有土地。
第四,規定了征地的補償標準。雖然堵上了老《辦法》里那兩個“不補償、不補助”的口子,明確征地補償包括土地補償、青苗補償、附著物補償和人員安置補助,但補償標準的立足點還是“維系農民生活”,而不是根據“被征用財產的市值”給予公平補償。特別是,規定了“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被征土地年產值的二十倍”,表明這是一道“管制補償上限”的法令。
最后,也是這部征地條例的最有特點之處,在于規定了征地程序,即由“用地單位”先行提出選址申請、與被征地單位協商訂約、經由行政審批、核定用地面積后,由政府向用地單位“劃撥土地”。這在操作上,等于由用地單位到政府辦了手續后,就可以實施征地。這就把商業利益和機構,引入了“國家征地”的過程。
上述“城鎮國有偏向”,集中反映在以下條款:“在征地過程中,煽動群眾鬧事,阻撓國家建設,貪污、盜竊國家和集體財物,行賄、受賄,敲詐勒索,以及其他違法犯罪行為,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至于“公家人”濫用征地權、侵占農民集體土地權益的,那除非貪污、受賄證據確鑿,一般也就給個不太重的行政處罰算了事。
這與1982年憲法推出“城市土地國有化”的背景是一致的,說明在當時的“上層建筑”里,對國家建設用地看得很重,但對征地過程中農民的土地權益,則看得比較輕。尤其對于土地利用的非征地通道或市場自由轉讓通道,在觀念上還不可想象、不可接受,所以在法律上就完全沒有留下空間。
1986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把過去的行政法規升格為國家法律。不過從內容看,以往征地法例的內容,基本全部裝進了新的《土地管理法》。換言之,土地利用方面的“城鎮國有偏向”,包括“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的虛置、征地通道的唯一合法性、禁絕土地的市場化利用、對征地補償實施上限管制,以及把商業利益和機構引入征地執行程序等等,差不多都法律化了。
此時還可能構成約束力的,僅剩下經濟實力了。因為征地的主體是政府和國有機構,所以國家征用土地的數量,總受到補償支付能力的硬制約。凡是付不出土地、青苗、附著物補償費和人員安置補助費的,事實上就完不成征地。霸王硬上弓的事各地所在都有,但行政的“霸力”講到底也是經濟力,在總體上限制著土地國有化的進度。
突破這重制約的,正是從1987年開始、1988年合法的“國有土地市場化”。在經濟上,“可預期的土地未來收益”支持了土地的資本化。在實務上,征地規模再也不受政府財力與用地機構預算的硬約束,市場里龐大的外資、內資、特別是充裕的銀行資本,都可以為征地提供融資。中國城鎮化從此有了完全不同于過去時代的經濟基礎。
為什么說征地權是其中的一把利器?答案是,離開了征地權,所謂“行政主導城鎮化”的三大支柱,包括城市土地屬于國家、城市設立的行政化機制以及城市國有土地的市場化交易,都缺乏“強制推進”的動力。在隱密的制度層面,商業利益、金融力量、土地資源與政府的合法強制力終于結合在一起,注定要開啟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