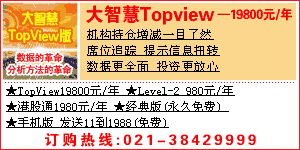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
他人眼中的諾曼·梅勒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18日 11:09 經(jīng)濟(jì)觀察報(bào)
郭娟 一天下午我在第四街和第八大道交叉處的一家咖啡館里,旁邊坐了兩個(gè)人,當(dāng)我們開(kāi)始交談,我發(fā)現(xiàn)其中一個(gè)人有濃重的得克薩斯口音,于是我問(wèn)他從哪兒來(lái)。 “紐約。”他說(shuō)。 “那你怎么會(huì)有那么重的得克薩斯口音?”我問(wèn)他。 “我在軍隊(duì)里呆過(guò)。” “在軍隊(duì)里呆過(guò)就會(huì)染上得克薩斯口音嗎?”我當(dāng)時(shí)的表情肯定沒(méi)有掩飾住我的好奇心。 “這基本上是一種保護(hù)色,”他說(shuō),“因?yàn)樵谲婈?duì)里,你要是個(gè)猶太人,他們就會(huì)給你起各種外號(hào),嘲笑你,讓你不好過(guò),所以我假裝來(lái)自得克薩斯。”他說(shuō)他離開(kāi)軍隊(duì)已經(jīng)八個(gè)月了,但這個(gè)老習(xí)慣還沒(méi)改掉。然后我們互相做了自我介紹。他的名字叫諾曼·梅勒。 ——馬龍·白蘭度,演員 我們那會(huì)兒住在皮爾朋特大街,那個(gè)街區(qū)通常都很安靜,不過(guò)一天下午,我忽然聽(tīng)見(jiàn)外邊一陣吵鬧聲,心想沒(méi)準(zhǔn)兒要發(fā)生什么暴力事件,于是打開(kāi)了大門,發(fā)現(xiàn)門口的臺(tái)階上坐著一個(gè)穿軍裝的小個(gè)子年輕男人,還有我樓上的漂亮女鄰居。他們看見(jiàn)我出來(lái)立刻安靜了下來(lái)。我想警報(bào)解除,就回到了公寓里。不過(guò)過(guò)了一陣子,我再次在街上見(jiàn)到了這個(gè)小個(gè)子男人,只不過(guò)這回他沒(méi)穿軍裝。他朝我走過(guò)來(lái),跟我說(shuō)他叫諾曼·梅勒,是個(gè)作家。他說(shuō)剛看了我的戲《我的諸子》。“我也能寫出這樣的戲來(lái)”,他說(shuō)。他說(shuō)得那么直接,我忍不住笑起來(lái),不過(guò)他對(duì)這件事可是百分之百的嚴(yán)肅認(rèn)真,而且在此后的多年里斷斷續(xù)續(xù)地做了些嘗試。那時(shí)我正苦心經(jīng)營(yíng)我的文學(xué)生涯,幾乎交不上什么朋友,但是梅勒看上去更像是要說(shuō)服我而不是來(lái)交什么朋友。雖然我們底子里很像,但是卻說(shuō)不到一起去。 總之,雖然有好多年我們彼此住得很近,但幾乎沒(méi)什么交集。 ——阿瑟·米勒,劇作家 1948年,我正在給 《紐約客》的“城中事”欄目寫東西,當(dāng)時(shí)梅勒剛剛出版了他的暢銷書 《裸者與死者》(他那時(shí)是個(gè)25歲的模樣好看的年輕人,藍(lán)眼睛,大耳朵,聲音柔和,有一股行事直接了當(dāng)?shù)淖雠伞C防諏?duì)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存在感到微微的不安,他覺(jué)得這兩個(gè)俄國(guó)人已經(jīng)把能寫的都寫盡了,而他自己,注定是要寫小說(shuō)的人)。后來(lái),我們成了朋友。我們互相跟對(duì)方坦白自己最想成為的人,我說(shuō)我要做世界上最好的女記者,他說(shuō)他要成為最棒的小說(shuō)家。 ——莉莉安·羅斯,《紐約客》記者 諾曼·梅勒起身講話,他是年輕的文學(xué)新星,仍處在《裸者與死者》帶來(lái)的盛名光環(huán)之下。梅勒說(shuō)美國(guó)和俄羅斯都在成為“國(guó)家資本主義”,他不得不表示他的悲觀——看起來(lái)和平是沒(méi)什么指望了。 演講結(jié)束后,我走過(guò)去對(duì)梅勒做自我介紹——離近了他看上去還像個(gè)小孩子——我說(shuō)我覺(jué)得他的演講很“誠(chéng)實(shí)”,他露齒而笑,帶著他自己特有的不是讓他更靠近天堂就是更接近地獄的古怪魅力。“不,”他說(shuō),“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誠(chéng)實(shí)。”我心想,得了,別裝了,不過(guò)我什么都沒(méi)有說(shuō)。我們約定了再次見(jiàn)面。 ——?dú)W文·豪,學(xué)者/批評(píng)家 新浪財(cái)經(jīng)獨(dú)家稿件聲明:該作品(文字、圖片、圖表及音視頻)特供新浪使用,未經(jīng)授權(quán),任何媒體和個(gè)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轉(zhuǎn)載。來(lái)源:經(jīng)濟(jì)觀察報(bào)網(wǎng)
【 新浪財(cái)經(jīng)吧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