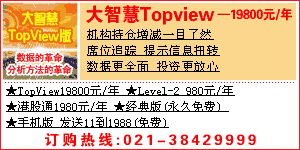|
|
|
郝建:為中國電影看病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18日 11:07 經濟觀察報
王小魯 個人身份的定位 郝建這些年來不停笑罵中國電影。他是北京電影學院電影學系的教授,主業是搞電影理論研究的。電影理論經常被看作是一個自足的小宇宙,是與某部具體影片沒有多大關系的自足的語言系統,郝建則經常能對新的電影現象及時進行回應,使得這些電影成為更大的話題,也動員了更多的人參與到這個爭論里來。對此,郝建有一種自覺意識,他覺得電影理論“經由評論是可以促進電影藝術形態的變化發展的,它可以讓研究者和創作者對電影的形式體系和當下活躍的文本更為自覺。” 雖然一些導演對于電影評論并不感興趣,聲稱自己不會受它們的影響,但事實上,卻有些導演根據這些呼聲來調整自己此后的創作,評論者與創作者一起塑造著中國電影的文化,只是這個經由文字的交流的效果經常被掩蓋掉了。 電影導演多是出產自電影學院,郝建沒有因此而為校友避諱,他批評電影的文章經常使他顯得不近人情。他這些年一直在批評一些第五代導演的電影作品,不久前張藝謀來到北京電影學院招翻譯,一個女生前來應聘,當女生報稱自己是電影學系的學生時,張藝謀馬上反應——就是那個天天有老師來罵我的那個系啊! 罵他的老師,以郝建最為有名。當然他并不只是為了罵而罵,有時候罵里有一種自我娛樂的成分,一種語言快感的追求,但也有問題意識和建設性。在第五代剛起步的時候,他也曾贊美第五代在形式和個性張揚方面的革命性。他說,他的批評其實是針對作品而來的,主要是電影中包含著的扭曲的意識形態的成分。 郝建搞過電影創作,對于電影中的形式比較敏感。他說他看電影像聽音樂一樣,能夠分析出其中的結構關系是否和諧。郝建編劇的《緊急迫降》曾獲得過華表獎,而且他熟悉電影剪輯等制作程序,所以能夠對一部電影進行細膩的技術分析。但是,電影對于郝建來說,主要還是幫他找到了一個比較及時的“公共話題”。目前的影評人有很多種,有一些是年輕人在報紙上寫的一些感性的評價文章,有的是比較學術的純粹技術分析,也有一些是自由知識分子以電影為話題,作為公共交流的一個契機和場合……郝介于后兩者之間,并主要是自覺以電影為公共話題展開與社會的對話。 影評人的價值和作用亦有所不同。有的影評主要是作為產品介紹,是電影產業鏈中的一環;還有一種注重的是電影作為時代精神的構成,注重研究電影在社會上傳播時的文化效應。郝的著力點則在后者。 郝建的另外一個比較自覺的工作定位,則是要進行更為廣泛的文化批評,他涉及的領域比較雜,他研究過電視劇,寫過各種公共藝術活動比如音樂會、實驗話劇的文化分析。 論“為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 總結他這些年的評論,最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是他批評第五代導演的幾位主將們不約而同的犬儒主義。第五代導演胡玫的《雍正王朝》的歌詞里有一句 “天下萬苦人最苦”,他從中聽出來的是“天下最苦,皇帝最苦”的聲音。他在張藝謀的《英雄》里看到了“荊柯護秦王”的一種犬儒主義和反動意識,他把《水滸傳》里的俠義只是看成了可怕的 “流竄做案”。最近又批評姜文的電影 《太陽照常升起》,分析了姜文在電影敘事上表現出來的表面的自由和內心的極端不自由,這同導演本人對文革的處理態度有關系。 他是怎么批評《太陽照常升起》的?他首先指出這是一種自說自話的文本,電影其實以商業片來進行操作,但因為蔑視觀眾而缺乏與觀眾的對話意識。更為關鍵的是,電影中關于文革的敘事使人感覺到了作者揀選記憶時的避重就輕和逃避—— “作者假裝看不到凌駕于我們生活之上的老大哥,卻硬把自己裝扮成一個誰都不理會,誰都不懼的老大哥,這是一種十分犬儒主義的態度……如果我們把形而下的感官享樂當作先鋒突破,如果我們在簡單的話語放縱中自鳴得意,我們把這種形而下的感官崇拜當作形而上的思想探尋,這就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犬儒主義。影片故意改寫歷史,它把一個黑暗年代涂抹成一個為鮮花盛開的村莊,把簡單的個人獨白當作必須讓觀眾去理解的深刻思想,這就是把犬儒主義當作英雄主義。” 郝建時常以一句話來形容一些作者的思想表情——“為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他說這句話時,針對的是那些反商業和全球化的學者們。其實,這句話既可以針對某些導演在創作電影時似乎是無意識下犯的錯誤,也可以針對整個學術界的另外一些現象。比如一些明星學者經常制造一些觀點,這些觀點看起來十分的有鋒芒也十分的真誠,比如有些學者的民族主義,比如“修繕自我,不要抱怨外在環境”,看起來這是發自內心的真誠思想表達,其實是經過了周詳的利益考慮后的發言。那些發言看起來頭頭是道,有時候甚至會讓人義憤填膺,顯得頗有正義感,其實是屁股決定大腦,只是為了做給權威看的“為得周郎顧,時時誤拂弦”。 這并不是認識能力的問題,而是愿不愿意認識的問題。這是一種猥瑣人格的矯情,其原因是其內心缺乏社會良心和一份真正的對于真理的敬畏。也許我們身邊的人甚至我們自己都會有這樣的狀況出現,但至少要有一個自我 自覺的意識,惟其如此,才不至于讓自己那么嚴肅地撒謊,甚至自己把自己都騙過了。 電影敘事活動如何影響社會? 郝建的影評與一些年輕人的影評不同,他寫影評有更多歷史經驗的參與,有比較充足的歷史感,比如他對于文革的話語十分敏感,總能從一些作品中看到文革的后遺癥,對于對那段歷史缺少認識的人來說,是不可能從電影中診斷出這樣的話語存在的。郝建認為文革話語對第五代乃至姜文這樣第五代之后的人有著非常深的影響,但人們也許會說,電影不過是一種娛樂,或者頂多是藝術,何必讓他們有那么多的負載呢,這會不會是一種泛政治化? 郝建認為若他們是單純的娛樂,他會以單純的娛樂來對待。事實上郝建一直在研究的領域是暴力美學,著重于研究一種純粹的形式趣味,他是欣賞暴力美學的,比如他在很早就四處推廣昆汀·塔倫蒂諾和吳宇森等導演的暴力場景的設計,但他也認為那種暴力美學需要一種良好社會體制和良好的文化空間來做底子。 他不反對暴力美學,卻反對“美學暴力”。什么是美學暴力?有一些導演在一些敘事場景中并沒有暴力的表象,其強硬灌輸價值觀的訴求卻是另外一種隱藏著的暴力行徑。郝建認為,電影是一個與社會的對話活動。電影敘事活動與社會精神活動之間的關系十分微妙、瑣細,不易覺察,卻并不是不重要的。 看電影能夠使人的經驗得以發展和開闊,時代精神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塑造。列寧曾將電影看成是所有文化形式中最為重要的藝術種類,他覺得電影是最能號召和影響大眾的。郝建在談類型電影的時候講到,類型電影的敘事活動作為一種藝術創作,和普遍的社會精神活動具有互動性和交流性,而現代人類的理性也正是在這種動態的、交往的過程中逐漸發展的,這就是現代化的過程。他相信哈貝馬斯說的,道德是在公共交往的過程中確立下來的,而非只屬于個人心靈的、先驗的。看電影、評電影自然都是這個社會交往的一個部分。 看來他并不認同商業電影的純粹性,這也就是他那么注重偵察電影透發出的錯誤價值觀和以寫影評來平衡其社會效應的一個動因。 呼吁娛樂,反對“硬作狂歡” 郝建是國內類型電影的主要研究者,而且也許是最早的。類型電影在美國很早就出現了,但是其研究專著卻是在20世紀80年代才出現。郝在1988年發表了研究類型電影的文章,背景就是由于當時娛樂片已經形成了一個不小的潮流,類型電影可以為娛樂片提供一個比較適合操作的方法。 郝建也是最早呼吁商業娛樂電影的學者之一。商業電影往往被看作缺乏思想性、平庸、體現粗淺的大眾水平。但郝建呼吁商業電影,也許有著另外一層的考慮,他認為呼吁商業和娛樂在當時中國是一個很有思想的思想。他對于周星馳的吹捧也是不遺余力的,據說周星馳的《大話西游》等電影在當時的中國并沒有得到廣泛的承認,只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幾次放映后,被電影學院的師生一起抬起來的。郝建也是其中的力量之一。 在國外的商業電影中,類型電影占有最大的比例,而且創造類型電影對于投資家來說,是商業風險相對較少的。類型電影在國內經常被看作是模式化的、淺薄的,但郝建卻贊美類型電影,因為類型電影里所包含的價值觀和形式趣味是平民化的,是在與平民觀賞趣味的交流中被固定并繼續發展著的。郝建這些年對于類型電影的推崇和商業電影的鼓吹,有很大一部分是看重了商業電影對于公民社會建設的作用。 郝建認為中國的類型片在解放前是比較發達的,到了80年代以后,又逐漸有了新的類型電影的出現,但到了90年代,商業類型片被主旋律電影所領導和抑制。現在類型片還在艱難的起步中。 他呼吁商業娛樂電影,但他反對硬作的狂歡,他出了一本書名叫《硬作狂歡》,分析那些看起來十分HIGH的歡樂表情其實是多么的虛偽,因為其內里空洞。有許多學者專門撰文批評中國的商業文化和由此生發出來的大眾文化,以之為批評的對象和靶心,并稱之為“大眾文化的狂歡”。郝建指出說這個是 “商業狂歡”是不對的,因為這不是真正的商業環境,那種商業文化的平民化的大狂歡在中國并未真正出現過。 出現過的,只是一些硬作的狂歡,是那些“把規定設計好的趣味當快感,把機械藝術規范的演繹當創作,把向中心單一價值觀的驅趕當成真的大眾自己的自由選擇。這種被限制的狂歡早就成為一種聽取將令以后訓練有素的美學齊步走……” 正如他批評姜文的《太陽照常升起》所說的:“如果我們把經過計劃、規定的笑聲當作真正的歡樂,把指令導向下的硬做狂歡當作是真正的縱酒放歌,這就是一種心知肚明卻照舊服從、歸順的犬儒主義。” 他反感的是中國電影中出現的集體主義的團體操般的美學風格,出現在觀眾面前的各種電視劇和電影,包括各類晚會的開幕式與主持者的情緒煽動,其實都因為過多的控制和過濾而逐漸喪失了真正活潑的精神,那些繁榮很少是真正體現大眾廣場上的笑聲的,而只是一種罐裝笑聲,或者說強制的煽情。這也許正是中國電影電視的敘事讓人覺得不自在的重要原因所在,因為它有著各種限制,不能徹底的自發自動,也就無法真正尊重接受者的趣味。 訪談 問:跟許多做電影理論的人不一樣,你寫的東西好像比較雜,除了電影評論,電視劇評論、奧運會開幕式、閉幕式的藝術設計這些你都評說過,你的文集《硬作狂歡》里還有一篇講聽音樂會的行為修養問題,這對一個學者會不會太分心而影響專業度? 郝:我的興趣比較廣泛,念本科時我寫的第一篇學生板報文章是講西方現代派美術……我寫過兩個電影劇本,上海電影廠拍攝的《緊急迫降》和紫禁城影業公司拍攝的《危情雪夜》,電視劇做的就多了,播出的有 《大屋的丫環們》、《真空愛情記錄》、《汽車城》、《沖出絕境》,對了,李揚《盲山》的拐賣婦女題材我在 2002年也寫過,當然,我寫電視劇必須要求寫出光明來,播出時叫《又見花兒開》。 問:你是理論教師,為什么要寫這些商業性的劇本? 郝:寫劇本掙錢多啊,這對我的生活和人的狀態有很大決定性。因為我手頭還不算窘迫,寫理論和評論就愛寫什么寫什么,愛怎么寫就怎么寫,我的假想讀者只有那些買報紙和雜志的人,我從來不會從影視公司拿錢寫東西。當然,去開會,吃人家的酒席是有的,鐘惦斐老師跟我們開玩笑地說過,吃人家的飯吃得嘴油油的哪里還說得出真話。 問:那你覺得你的主要興趣在哪里? 郝:寫評論和創作都是在尋求一種語言表達的美感,我的興趣在于探索文字的結構和肌理,我在這文字的編織、推敲、緊縮和飛揚中得到一種快感。另一種快感是來自于跟其他人、跟社會的交流,或者簡單說滿足自己的表達欲吧,我有文化批評的情結,又有比較清醒地與各種意識形態和藝術趣味進行對話的愿望。但是我在寫作上,在話語上明顯感覺到自己是在向一種非常平實的明白的話語上進行轉換,這個是我有意識做的。如果說文本上的標桿吧,我覺得這個要說到王小波和王朔——主要是王小波,這是我自覺追求的,包括我寫了文章請一些朋友看,我追求講大白話。 問:從你的評論和創作來看,你一直把大陸的大眾文化作為積極元素來評價,現在回過頭來看,你的許多觀點是不是有所改變? 郝:對大眾文化我是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評價,我不滿意大陸一些挺時髦的觀點,簡單地把大眾文化當作一個庸俗甚至低俗的東西,當作是已經成為權威文化的東西來加以警惕和抵制。在這方面,我對當下語境的總體估計沒有變,大的思路、價值觀也沒有改變。 問:近幾年你好像對第五代導演的作品有許多批判,主要觀點是什么? 郝:對于作為創作者的第五代導演,我從來沒有在整體上批評他們,我試圖從具體作品來剖析我們的文化心理,我們當下社會的文化走向和一些作品的價值取向——從第五代導演后來的一些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大陸文化創作、文化產品、文化人的心理結構與中國市民社會和權威的意識形態的關系。具體說到第五代導演,我對他們在新時期到上世紀90年代的一些作品比較喜歡。你去查《文匯電影時報》,1992年我有一篇《扛著累累碩果的張藝謀》,我對于那時的張藝謀的創作,不管是從創作還是文化心理上,都是很欣賞的張藝謀的 《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表現出來一種現實主義的精神和對個性解放的呼喚。作品里有對人的個體選擇的肯定,在電影語言形式上也有一種強烈的創新沖動,比如《黃土地》呈現了導演的語言突破能力,這里面有他們個體力量的一個爆發。一直到今天來看,這些東西還是有它的積極價值。 問:你對張藝謀的評價有一個轉變,好像是從《一個都不能少》開始,一直到他拍攝大片。 郝:對,我對張藝謀的作品有一個簡單的劃線,一直到他的 《有話好好說》,我都很喜歡。從《一個都不能少》開始,張藝謀的作品和在報紙電視上的社會表態都出現向主導性的話語轉移的趨勢。陳凱歌呢,他的電影和權威的關系比較復雜,他一直是肯定和追尋人的個體自由,但是他的心理價值觀上集體主義的內容更多些。他的《大閱兵》就有向集體主義價值觀靠攏的傾向,當然要細說不那么簡單,可能是一種揮之不去的迷思,有時是在批判和對抗中的臣服……不是說他要討好誰啊,獻媚誰啊,他并不是有意識地要這樣做,我想研究的是他在文化心理上與權威的關系,或者在美學上他和權威話語、流行的藝術觀念的關系。對于權威的一種崇拜和不自覺的一種受虐心理,我的分析是他們青春期既當紅衛兵又受到傷害的心理后遺癥。比如說從《大閱兵》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種集體主義的價值觀,那里面似乎有對整體、紀律、威嚴的隊伍和空曠廣場上整齊步伐的力量的表現,當然這是對抗還是不自覺的臣服和崇拜還有具體讀解文本來分析。從我的價值觀來看,我對這種過分整體性的、從集體性主義的價值觀去塑造人是持批評態度的。這在中國當代社會走向現代化、走向個體的覺醒、走向公民社會的過程中是一些負面的價值觀。 問:其實你是要分析電影中所呈現的集體無意識,包括你前段時間對于姜文的電影 《太陽照常升起》的批評,他們的電影作為集體無意識的呈現給你提供了一個話題,也許你并不僅僅針對某個具體人,其實是把他們的作品看為整個社會的病歷。 郝:對,他們的作品只不過給我跟社會對話找到一個契機,一個大家都認識的標本。他們的作品是作為社會的一種文化而存在的。我在尋求電影的形式快感的同時也在分析他們的電影創作背后的文化心理,比如說《太陽照常升起》是一種非常暴力的話語,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權威的話語。作者的創作心態很有趣,就好像一個偉人在朗誦自己的詩篇,所以在美學上和在藝術理念上他用了大量的比較強力表達意念的雜耍蒙太奇,所以他有大量對觀眾的直接喊話,大量的非敘事性的話語,導演時常對觀眾自言自語,比如他讓瘋媽說:“你可以說你不懂,但你不能否認你看見了。”這如果是自己寫的詩歌拿到博客或者文學雜志上去發或許很美麗,但在講究對話、交流的商業電影中是很強勢的,是犯規的。 問:有很多觀點持有者,可能會覺得你對大眾文化、商業性這一塊過于樂觀了。 郝:我是從提倡文化的豐富性、提倡我們民族的藝術活力和創造力的角度來抨擊文革意識形態的。大陸是趣味饑渴、幽默饑渴、故事饑渴,所以看到出了一個 《瘋狂的石頭》,整個大陸文化界、評論界就歡呼雀躍。當然,有的人認為趣味的單一化和被壓制是由于資本的原因,由于商業社會的原因,由于金錢的原因;我看到的正相反,商業交換這一套機制提供了藝術創造的天地。從某個角度來說,我們提供的藝術就是在金錢當中交換的,就是在交換中完成的創造,你說是銅臭也好,鮮花就是和金錢的閃光一道煥發出它的魅力的。我們要仔細具體分析,到底是全球化、市場經濟秩序,還是管理上的體制性制約、公平規則的缺失壓抑了電影的創作。 問:你一直在研究類型電影,類型片的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對于電影商人來說,操作類型電影的商業風險是比較小的。 郝:它是一種約定俗成,是對于觀眾的趣味、心理,還有倫理、價值的一種尊重。最重要的,它的規范不是那幾個人單向設計的,是在跟觀眾的反復交流中自然形成的,這與哈貝馬斯說的交往中建立的理性、交往的合法性完全符合。最近我看姜文的《太陽照常升起》,他那里面是不講故事的,我就順著他的趣味反過來思考,電影可不可以不講故事?為什么電影要講故事?你看好萊塢的商業電影主要是講故事,而且一定要把故事講好。一定要講故事,這是因為什么呢?因為這樣大家可以互相理解,它是一種對話。講故事不是一種宣告性的話語,不是一種獨斷性的話語,講故事其實是一種理性的對話并且在發揚一種對話中的理性。 新浪財經獨家稿件聲明:該作品(文字、圖片、圖表及音視頻)特供新浪使用,未經授權,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轉載。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 新浪財經吧 】
不支持Fla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