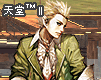| 集體產權:被遺忘的“角落”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4月11日 15:16 中國經營報 | |||||||||
|
作者:泰山 國內日化界率先扛起民族品牌大旗的重慶奧妮的“假合資”事件和圍困董事長黃家齊事件引起了公眾對奧妮的關注。而黃家齊與奧妮職工間持續了近3年的企業產權和企業資產糾紛驟然升級,又一次進入公眾視線。這一事件,使經濟學界和輿論界再次重新拾起一個已經被“遺忘”的話題,曾經在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貢獻的集體企業產權歸屬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有的集體企業由于快速發展,過渡到了全民所有制。而很多企業則依然屬于集體企業,比如曾經試圖企業產權改革的春蘭集團。 按照產權理論,財產所有權是通過以下四項權利來體現的:(1)經營者的選擇權,(2)經營決策權,(3)財產收益權,(4)財產最終處置權。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理論上屬于該企業全體職工所有,職工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利機構,行使所有權。但在實踐中集體所有制企業存在著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 首先,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所有者實際上很難實施各種所有者的權利。例如,如何選擇經營者,全體職工雖然在理論上具有這種權利,但事實上卻難以實施,因為普通職工不具備選擇經營者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和決策依據,這就是一個矛盾,而且企業越大,難度也越大。由于集體企業自身無法解決經營者選擇問題,政府主管部門也就逐步替代了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現在稍有規模的集體企業,經營者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門委派。奧妮的案例中,企業的職工實際上無法行使自己的權利。 其次,集體所有制企業同樣存在“內部人控制”問題,甚至比國有企業更加嚴重。比如奧妮的案例中,企業實際上一直被黃控制著。而政府對集體企業的監管多少有點名不正言不順,集體企業擁有更大的經營自主權,企業更容易被經營者控制。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通職工無法對企業重大經營決策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而只能聽任經營者決斷,職工代表大會幾乎只是一種形式。 集體所有制企業事實上存在“經營者控制”,所以由現任經營者自己挑選接班人就有可能對企業并不是最合理——現任經營者挑選接班人的首要標準往往是聽話,而不是經營才能,因為只有聽話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延續自己的控制力。所以,在挑選接班人問題上企業經營者往往和政府不一致,這時政府不得不再次代替集體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為企業做出選擇和決策。如果政府選擇錯了,政府也不可能承擔責任,這正是集體企業制度性的悲劇所在。 再次,集體所有制企業也存在產權虛置、所有者對資產關切度不高的問題。集體企業產權雖然屬于企業全體職工所有,但資產不能量化到個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狀況與資源的自由流動是有直接沖突的,職工在企業是所有者,一旦離開企業就會喪失這種所有者地位。同時,也阻礙新員工的進入,新員工進入集體企業是否要帶資?如果不帶資,就會形成對原有老員工財產所有權的剝奪,所以集體所有制企業有天然的排斥新員工的傾向。 那么,集體企業產權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從1992年國家有過《集體企業條例》之外,10多年來,對集體企業的資產歸屬、發展、監管等成長過程中的新問題,無任何新的政策出臺。奧妮的黃家齊曾經嘗試多次在法律情況下的產權改革,但現實是找不到相應的法律根據。2000年曾經嘗試產權改革的春蘭集團,也由于沒有相關的法律根據,最終的產權改革也被迫叫停。 根據實踐,中國鄉鎮集體企業產權的改革邏輯是:企業控制權向經理層轉移、經理報酬與企業利潤掛鉤,直到比較完整的企業剩余權的形成及其資本化,最后發展出地方資本市場來交易資本化的企業家人力資本。 而目前最為緊迫的幾個任務則是,盡快界定集體企業的產權邊界。集體企業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政府已習慣將它視同國有企業,但是它在產權屬性的諸多方面又不屬于國有企業,但政府將許多國有企業優惠政策給了集體企業,導致集體企業在產權邊界上比較模糊。 如何量化到個人也是一件很復雜的工作,經營者與普通員工之間,新老員工之間,正式工與臨時工之間,以及有償量化還是無償量化等等,都需要從企業的實際出發。量化到個人以后,應當允許已經量化的股權在一定的規則下自由轉讓,以及向企業外部投資者開放,只有自由轉讓才可能實現股權的相對集中,產生大股東,降低企業的制度成本,形成有效率的現代企業制度。 奧妮的案例,也許能提醒人們對集體所有制的改革多一些關注,盡快將集體企業的產權改革推向縱深。國內日化界率先扛起民族品牌大旗的重慶奧妮的“假合資”事件和圍困董事長黃家齊事件引起了公眾對奧妮的關注。而黃家齊與奧妮職工間持續了近3年的企業產權和企業資產糾紛驟然升級,又一次進入公眾視線。這一事件,使經濟學界和輿論界再次重新拾起一個已經被“遺忘”的話題,曾經在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貢獻的集體企業產權歸屬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有的集體企業由于快速發展,過渡到了全民所有制。而很多企業則依然屬于集體企業,比如曾經試圖企業產權改革的春蘭集團。 按照產權理論,財產所有權是通過以下四項權利來體現的:(1)經營者的選擇權,(2)經營決策權,(3)財產收益權,(4)財產最終處置權。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理論上屬于該企業全體職工所有,職工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利機構,行使所有權。但在實踐中集體所有制企業存在著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 首先,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所有者實際上很難實施各種所有者的權利。例如,如何選擇經營者,全體職工雖然在理論上具有這種權利,但事實上卻難以實施,因為普通職工不具備選擇經營者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和決策依據,這就是一個矛盾,而且企業越大,難度也越大。由于集體企業自身無法解決經營者選擇問題,政府主管部門也就逐步替代了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現在稍有規模的集體企業,經營者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門委派。奧妮的案例中,企業的職工實際上無法行使自己的權利。 其次,集體所有制企業同樣存在“內部人控制”問題,甚至比國有企業更加嚴重。比如奧妮的案例中,企業實際上一直被黃控制著。而政府對集體企業的監管多少有點名不正言不順,集體企業擁有更大的經營自主權,企業更容易被經營者控制。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通職工無法對企業重大經營決策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而只能聽任經營者決斷,職工代表大會幾乎只是一種形式。 集體所有制企業事實上存在“經營者控制”,所以由現任經營者自己挑選接班人就有可能對企業并不是最合理——現任經營者挑選接班人的首要標準往往是聽話,而不是經營才能,因為只有聽話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延續自己的控制力。所以,在挑選接班人問題上企業經營者往往和政府不一致,這時政府不得不再次代替集體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為企業做出選擇和決策。如果政府選擇錯了,政府也不可能承擔責任,這正是集體企業制度性的悲劇所在。 再次,集體所有制企業也存在產權虛置、所有者對資產關切度不高的問題。集體企業產權雖然屬于企業全體職工所有,但資產不能量化到個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狀況與資源的自由流動是有直接沖突的,職工在企業是所有者,一旦離開企業就會喪失這種所有者地位。同時,也阻礙新員工的進入,新員工進入集體企業是否要帶資?如果不帶資,就會形成對原有老員工財產所有權的剝奪,所以集體所有制企業有天然的排斥新員工的傾向。 那么,集體企業產權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從1992年國家有過《集體企業條例》之外,10多年來,對集體企業的資產歸屬、發展、監管等成長過程中的新問題,無任何新的政策出臺。奧妮的黃家齊曾經嘗試多次在法律情況下的產權改革,但現實是找不到相應的法律根據。2000年曾經嘗試產權改革的春蘭集團,也由于沒有相關的法律根據,最終的產權改革也被迫叫停。 根據實踐,中國鄉鎮集體企業產權的改革邏輯是:企業控制權向經理層轉移、經理報酬與企業利潤掛鉤,直到比較完整的企業剩余權的形成及其資本化,最后發展出地方資本市場來交易資本化的企業家人力資本。 而目前最為緊迫的幾個任務則是,盡快界定集體企業的產權邊界。集體企業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政府已習慣將它視同國有企業,但是它在產權屬性的諸多方面又不屬于國有企業,但政府將許多國有企業優惠政策給了集體企業,導致集體企業在產權邊界上比較模糊。 如何量化到個人也是一件很復雜的工作,經營者與普通員工之間,新老員工之間,正式工與臨時工之間,以及有償量化還是無償量化等等,都需要從企業的實際出發。量化到個人以后,應當允許已經量化的股權在一定的規則下自由轉讓,以及向企業外部投資者開放,只有自由轉讓才可能實現股權的相對集中,產生大股東,降低企業的制度成本,形成有效率的現代企業制度。 奧妮的案例,也許能提醒人們對集體所有制的改革多一些關注,盡快將集體企業的產權改革推向縱深。國內日化界率先扛起民族品牌大旗的重慶奧妮的“假合資”事件和圍困董事長黃家齊事件引起了公眾對奧妮的關注。而黃家齊與奧妮職工間持續了近3年的企業產權和企業資產糾紛驟然升級,又一次進入公眾視線。這一事件,使經濟學界和輿論界再次重新拾起一個已經被“遺忘”的話題,曾經在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貢獻的集體企業產權歸屬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有的集體企業由于快速發展,過渡到了全民所有制。而很多企業則依然屬于集體企業,比如曾經試圖企業產權改革的春蘭集團。 按照產權理論,財產所有權是通過以下四項權利來體現的:(1)經營者的選擇權,(2)經營決策權,(3)財產收益權,(4)財產最終處置權。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理論上屬于該企業全體職工所有,職工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利機構,行使所有權。但在實踐中集體所有制企業存在著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 首先,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所有者實際上很難實施各種所有者的權利。例如,如何選擇經營者,全體職工雖然在理論上具有這種權利,但事實上卻難以實施,因為普通職工不具備選擇經營者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和決策依據,這就是一個矛盾,而且企業越大,難度也越大。由于集體企業自身無法解決經營者選擇問題,政府主管部門也就逐步替代了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現在稍有規模的集體企業,經營者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門委派。奧妮的案例中,企業的職工實際上無法行使自己的權利。 其次,集體所有制企業同樣存在“內部人控制”問題,甚至比國有企業更加嚴重。比如奧妮的案例中,企業實際上一直被黃控制著。而政府對集體企業的監管多少有點名不正言不順,集體企業擁有更大的經營自主權,企業更容易被經營者控制。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通職工無法對企業重大經營決策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而只能聽任經營者決斷,職工代表大會幾乎只是一種形式。 集體所有制企業事實上存在“經營者控制”,所以由現任經營者自己挑選接班人就有可能對企業并不是最合理——現任經營者挑選接班人的首要標準往往是聽話,而不是經營才能,因為只有聽話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延續自己的控制力。所以,在挑選接班人問題上企業經營者往往和政府不一致,這時政府不得不再次代替集體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為企業做出選擇和決策。如果政府選擇錯了,政府也不可能承擔責任,這正是集體企業制度性的悲劇所在。 再次,集體所有制企業也存在產權虛置、所有者對資產關切度不高的問題。集體企業產權雖然屬于企業全體職工所有,但資產不能量化到個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狀況與資源的自由流動是有直接沖突的,職工在企業是所有者,一旦離開企業就會喪失這種所有者地位。同時,也阻礙新員工的進入,新員工進入集體企業是否要帶資?如果不帶資,就會形成對原有老員工財產所有權的剝奪,所以集體所有制企業有天然的排斥新員工的傾向。 那么,集體企業產權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從1992年國家有過《集體企業條例》之外,10多年來,對集體企業的資產歸屬、發展、監管等成長過程中的新問題,無任何新的政策出臺。奧妮的黃家齊曾經嘗試多次在法律情況下的產權改革,但現實是找不到相應的法律根據。2000年曾經嘗試產權改革的春蘭集團,也由于沒有相關的法律根據,最終的產權改革也被迫叫停。 根據實踐,中國鄉鎮集體企業產權的改革邏輯是:企業控制權向經理層轉移、經理報酬與企業利潤掛鉤,直到比較完整的企業剩余權的形成及其資本化,最后發展出地方資本市場來交易資本化的企業家人力資本。 而目前最為緊迫的幾個任務則是,盡快界定集體企業的產權邊界。集體企業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政府已習慣將它視同國有企業,但是它在產權屬性的諸多方面又不屬于國有企業,但政府將許多國有企業優惠政策給了集體企業,導致集體企業在產權邊界上比較模糊。 如何量化到個人也是一件很復雜的工作,經營者與普通員工之間,新老員工之間,正式工與臨時工之間,以及有償量化還是無償量化等等,都需要從企業的實際出發。量化到個人以后,應當允許已經量化的股權在一定的規則下自由轉讓,以及向企業外部投資者開放,只有自由轉讓才可能實現股權的相對集中,產生大股東,降低企業的制度成本,形成有效率的現代企業制度。 奧妮的案例,也許能提醒人們對集體所有制的改革多一些關注,盡快將集體企業的產權改革推向縱深。 |
| 首頁 ● 新聞 ● 體育 ● 娛樂 ● 游戲 ● 郵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點卡 ● 天氣 ● 答疑 ● 交友 ● 導航 |
| 新浪首頁 > 財經縱橫 > 產經動態 > 正文 |
|
| |||||||||||||||||||||||||||||||
|
新浪網財經縱橫網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指正 新浪簡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 | 聯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員注冊 | 產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