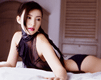|
華盛頓和拿破侖的心靈,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華盛頓的身邊,全是些商人和法律家,他們是美國的立國者、制憲者。其實,商人和法律家具有類似的精神氣質。
“法律家”的英文雖然是lawyer,但這個lawyer的意思,不只是指我們所理解的“律
師”,而有更廣泛的含義。在普通法傳統中,法律不是立法者創制出來的,而是由法律家創造出來的。他們首先是律師,部分資深律師會成為法官。法官和律師在法庭上,通過對個別案件的審理,為社會立法。
關于這些法律家的精神氣質,愛德蒙·柏克有過精彩的描述。在《論與美洲和解的演講》(中文譯文收入繆哲譯《美洲三書》)中曾經討論過法律精神,如何促進了美洲殖民地的自由精神,使其勇敢地反對英國對殖民地的高壓政策。
根據柏克的觀察,在北美,“法律研究的普遍,也許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如此之甚的。這一職業人數很多,且勢力頗大;在多數的省中,它都是執牛耳者。派往會議(此指第一次大陸會議)的代表們,曾有很多是律師。而所有識字的人、大多數讀書的人,莫不努力從事這一門科學里,獲取一星半點的知識。”
柏克在這里說的是大陸會議。后來的美國費城制憲會議,各州派來的代表,也多是法律家:或者當過法官,或者當過律師,即使從事別的事業,也受過法律教育。
柏克接著說:“法律的研究,每使人敏銳、善察、機巧,每使人果于殺伐,巧于防御,富于智謀。他國的人,頭腦較他們單純,性格比他們遲鈍,只依既成的苦難,論斷政治中的病因;而在美洲,他們則依據原則的不良,預見弊端、判斷苦難的輕重。他們卜見秕政于千里之外;從每一腐臭的微風里,嗅知暴政的來臨。”
柏克的父親是一位律師,柏克本人也曾經學習過法律。而在當時他所活躍的英國政界,大半人物也受過法律教育。因而,柏克的評論是極為精當的。比如,上引最后一句話,阿克頓就可以作個佐證。他在《法國大革命講稿》中評論說,“美國在一種根本不足以發動一場叛亂的挑釁面前奮起反抗取得了獨立”。
這樣的法律精神,在美國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反過來,在法國,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文人情調。
國內總有些小資談論“左岸”,筆者始終不解其意。最近查閱資料才知道,原來是指巴黎塞納河左岸,文人們活動的場所。從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前夕,政治家、哲學家經常在貴夫人的沙龍和塞納河左岸的咖啡館里討論哲學和政治。當年羅伯斯·庇爾與馬拉們聚會的塞納河左岸的老咖啡店,一直保留至今天。有一首歌——《巴黎天空下》是這樣唱的:“巴黎天空下,坐著一位哲學家,兩位樂師,和一群看熱鬧的乞丐和流浪漢。四方游客云集,他們海闊天空地神聊。”正是這些人,聊出了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以及五花八門的哲學和政治運動。
文人情調,本是很有情調的東東,但是,一旦社會、政治革命滲透著文人情調,那可就麻煩了。
作者:秋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