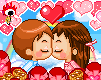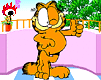| 后鄧小平時(shí)代 | |||||||||
|---|---|---|---|---|---|---|---|---|---|
|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8月21日 10:28 經(jīng)濟(jì)觀察報(bào) | |||||||||
|
轉(zhuǎn)折點(diǎn) “偉大的轉(zhuǎn)折時(shí)刻”出現(xiàn)在這一年的12月18日至22日的5天里, 290名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在建成于1959年的人民大會(huì)堂參加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曾目睹了清王朝的衰落和軍閥混戰(zhàn),親身經(jīng)歷了艱苦的長(zhǎng)征,抗擊了日本的入侵并贏得內(nèi)戰(zhàn)。在激情洋溢地參與建立新中國(guó)8年后,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又被卷進(jìn)了另一場(chǎng)浩大的動(dòng)亂——他們同意
“開放”往往要比“改革”更早發(fā)生。1978年12月19日,也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召開后的第二天,總部在美國(guó)西雅圖的波音公司宣布中國(guó)將訂購(gòu)3架波音747飛機(jī);也是在這一天,可口可樂公司董事會(huì)主席宣布,已與中國(guó)達(dá)成協(xié)議在上海設(shè)立瓶裝廠,向這個(gè)將近10億人的市場(chǎng)銷售它的碳酸飲料。一個(gè)多月后的1月29日,鄧小平以副總理的身份出訪美國(guó),剛剛在幾周前被《時(shí)代》評(píng)選為年度人物的他戴上了牛仔帽。23天前的1月5日,時(shí)任安徽省第一書記的萬里對(duì)鳳陽(yáng)縣委書記陳庭元說:“單干也沒什么了不起。” 新的開端總是以清理舊遺產(chǎn)開始。早在1977年復(fù)出前,鄧小平就已直言不諱地攻擊了“兩個(gè)凡是”,而到了1980年,他應(yīng)該更為清晰地表達(dá)他對(duì)他的前任的看法。“我們不會(huì)像赫魯曉夫?qū)Υ勾罅帜菢訉?duì)待毛主席。”在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采訪時(shí),鄧小平說天安門上毛主席像要永遠(yuǎn)保留,他說盡管毛澤東在生命中的最后時(shí)光犯下了錯(cuò)誤,但是他多次將黨和國(guó)家在危機(jī)中挽救出來,如果沒有他,至少中國(guó)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zhǎng)的時(shí)間。而就在說出這番話的三個(gè)月前,鄧小平領(lǐng)導(dǎo)的第二代領(lǐng)導(dǎo)集體,完成了對(duì)劉少奇的平反。在文革中,劉少奇是比鄧本人更“反動(dòng)”的“第一號(hào)走資派”,“平反”本身就意味著否定了毛澤東的決定。鄧小平用“三七開”來評(píng)價(jià)毛澤東,但在當(dāng)時(shí)的氣氛下,人們顯然對(duì)那三分錯(cuò)誤更為印象深刻——一個(gè)神話般的人物竟然也會(huì)犯錯(cuò)誤。 也是在這一年里,“四人幫”被宣判,華國(guó)鋒辭去了最后兩個(gè)重要職務(wù)——中央委員會(huì)主席與中央軍委主席,分別由胡耀邦與鄧小平接替。 要想了解這段歷史,沒有什么比《鄧小平文選》第二卷更好的文獻(xiàn)了。與毛澤東恣意汪洋的文風(fēng)不同,鄧的講話簡(jiǎn)潔、樸素,政治學(xué)家鄒讜說它“有時(shí)甚至是漫談式的”。而比起毛對(duì)理論的愛好,鄧小平基本很少引用馬克思理論家們的術(shù)語,鄒讜還發(fā)現(xiàn)斯大林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被并列提了三次,斯大林還被單獨(dú)提到了三次,其中一次意味深長(zhǎng):“斯大林嚴(yán)重破壞社會(huì)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guó)家不可能發(fā)生。他雖然認(rèn)識(shí)到這一點(diǎn),但是由于沒有在實(shí)際上解決領(lǐng)導(dǎo)體制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dǎo)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政治改革 多年以后,人們往往習(xí)慣將鄧小平視作一場(chǎng)偉大的經(jīng)濟(jì)革命的設(shè)計(jì)師。這種評(píng)價(jià)既低估了他,也誤解了中國(guó)社會(huì)。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只記住了“科學(xué)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社會(huì)主義也可以有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按需分配”,“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不管白貓黑貓,”,“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致富光榮”,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鄧小平在政治與軍隊(duì)問題上同樣深遠(yuǎn)的影響。在1984年10月6日,他相當(dāng)誠(chéng)實(shí)的說,在經(jīng)濟(jì)問題上,他是個(gè)外行,而所講的話,都是從政治角度來說的。而在同一天的會(huì)議上,他說進(jìn)入小康社會(huì),也是一個(gè)政治目標(biāo)。 翻開第二卷文獻(xiàn),47篇講話幾乎覆蓋了中國(guó)改革的每一個(gè)方面,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他對(duì)毛澤東思想的再闡述,對(duì)于黨與領(lǐng)導(dǎo)制度的改革,對(duì)于軍隊(duì)改革的建議,對(duì)于民主與法制的要求,對(duì)于中國(guó)在世界應(yīng)扮演的角色……他從70年代末起對(duì)美國(guó)、東南亞等國(guó)的訪問,有力地消除了中國(guó)在文革中樹立起來的咄咄逼人、輸出革命的國(guó)家形象;他大膽地做出了和平是世界的主旋律的判斷;他進(jìn)行的軍隊(duì)改革,則試圖使軍隊(duì)現(xiàn)代化;他開始精減機(jī)構(gòu),動(dòng)員老干部退休,推動(dòng)干部的年輕化,他自己則對(duì)個(gè)人崇拜毫無興趣,沒有興趣擔(dān)當(dāng)過多的職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號(hào)……在經(jīng)歷了一個(gè)變幻無常的時(shí)代之后,鄧小平試圖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縮小領(lǐng)導(dǎo)人的個(gè)人品質(zhì)、權(quán)力、威望的影響因素。 1984年 1984年是鄧小平一生中的巔峰時(shí)刻之一,就像1949年之于毛澤東,或是1911年之于孫中山。距離1978年那個(gè)“偉大的轉(zhuǎn)折時(shí)刻”已經(jīng)5年,中國(guó)正在掙脫令人窒息與一片茫然的氛圍。農(nóng)村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中國(guó)社會(huì)似乎從未生產(chǎn)過足夠的糧食,但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做到了。鄧小平在1983年初視察江蘇、浙江與上海等地時(shí)發(fā)現(xiàn),“人們喜氣洋洋、新房子蓋得很多、市場(chǎng)物資豐富,干部信心很足”。一股樂觀情緒鼓舞著整個(gè)社會(huì),在通過“傷痕文學(xué)”盡情發(fā)泄對(duì)于往日的不滿與失望之后,開放所帶來的源源不斷的新事物也讓人們目瞪口呆:1979年1月28日,上海電視臺(tái)為參桂補(bǔ)酒播放了中國(guó)第一條電視廣告;在首都機(jī)場(chǎng)里出現(xiàn)了正面女人裸體畫;1980年,北大的學(xué)生開始民主選舉學(xué)生會(huì)主席;個(gè)體戶成了富裕的代名詞,1982年有人穿上了牛仔褲;1983年北京農(nóng)展館里首次舉辦了時(shí)裝表演;1984年,紡織部52歲的女部長(zhǎng)吳文英出差時(shí)穿上了線條流暢的裙子……國(guó)家情緒的改變當(dāng)然不僅僅存在于物質(zhì)層面,一些集體性的事件也正在使得這個(gè)被漫長(zhǎng)的戰(zhàn)爭(zhēng)與內(nèi)亂弄得精疲力竭的民族重新獲得想象力,中國(guó)女排在1981年獲得了世界冠軍,1982年11月的第九屆亞運(yùn)會(huì)上,中國(guó)獲得金牌數(shù)量首次超過了日本,而在1984年7月,許海峰在洛杉磯摘取了中國(guó)首枚奧運(yùn)金牌,在那次仍被冷戰(zhàn)籠罩的競(jìng)賽上,因蘇聯(lián)的抵制,中國(guó)獲得了金牌數(shù)量第三的成績(jī)…… 對(duì)于這個(gè)國(guó)家和鄧小平本人來說,這一連串的興奮在1984年10月1日迎來了高潮。那一天,80歲的鄧小平橫穿天安門廣場(chǎng),耳邊回蕩的是上百萬人此起彼伏的呼喊——“首長(zhǎng)辛苦了”。這一次的大閱兵讓在場(chǎng)的德國(guó)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大為震驚,他后來頗富情感地回憶說:“作為國(guó)防軍的一名年輕士兵以及30年后作為國(guó)防部長(zhǎng),我學(xué)會(huì)了不那么重視閱兵式。但在天安門廣場(chǎng)上沿長(zhǎng)安街那場(chǎng)壯觀的表演確實(shí)是壓倒一切的。誰要是在電視中看到洛杉磯的奧運(yùn)會(huì)開幕式,他就可以設(shè)想一下,把洛杉磯體育場(chǎng)上的演員人數(shù)用100再乘出一個(gè)數(shù)就是所看到的情況:五彩繽紛的大小彩旗,很多大的絳紅色的氣球和成千上萬只小氣球懸在廣場(chǎng)上空,還有50萬人身著艷服圍成大圈跟著樂曲跳舞。”而在閱兵式后,施密特看到了“望不到盡頭、五彩繽紛、扣人心弦和輕松歡快的游行隊(duì)伍,他們由來自全國(guó)各行各業(yè)的代表隊(duì)組成。” 在天安門這座象征著傳統(tǒng)皇權(quán)的城樓上,鄧小平說“我國(guó)的經(jīng)濟(jì)獲得了空前的蓬勃發(fā)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認(rèn)的成就。今天,全國(guó)人民無不感到興奮和自豪。”而對(duì)于很多人來說,這種興奮與自豪的高潮來自于這一時(shí)刻:一群由年輕人組成的方隊(duì)在經(jīng)過觀禮臺(tái)時(shí),一幅制作簡(jiǎn)陋、由歪歪扭扭的“小平,你好”四個(gè)組成的橫幅,被意想不到地舉了起來。這個(gè)本應(yīng)被嚴(yán)格禁止的舉動(dòng),日后成了20世紀(jì)中國(guó)最重要的場(chǎng)景。這個(gè)自發(fā)的舉動(dòng),更有力的表現(xiàn)出公眾對(duì)于一位政治領(lǐng)導(dǎo)人的親密情感。比起18年前天安門廣場(chǎng)上的迷狂,這一時(shí)刻充滿真摯卻冷靜的熱情。 80天后,時(shí)任國(guó)務(wù)院總理的趙紫陽(yáng)與英國(guó)首相撒切爾夫人在人民大會(huì)堂簽署了《中英聯(lián)合聲明》。這是鄧小平一生中又一個(gè)歷史性的時(shí)刻。他18歲加入革命,23歲成為中共中央書記,25歲領(lǐng)導(dǎo)百色起義,一直到45歲前都是在國(guó)內(nèi)戰(zhàn)爭(zhēng)與抗日戰(zhàn)爭(zhēng)中度過的,62歲以后又經(jīng)歷了劇烈的社會(huì)動(dòng)蕩……像他那一代或再年長(zhǎng)的幾代人一樣,他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承受的一切痛苦、遭遇的種種挫折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中國(guó)獲得她失落的尊嚴(yán)。香港是這一連串屈辱中的第一個(gè),即使毛澤東在1949年新中國(guó)成立時(shí),也未能消除這一舊遺產(chǎn)。在與鄧小平的兩次會(huì)面中,撒切爾夫人發(fā)現(xiàn)這個(gè)在會(huì)談中要在腳邊擺一個(gè)痰盂的老人,態(tài)度堅(jiān)定、執(zhí)著并驚人的直率。一個(gè)過于戲劇化并被時(shí)常提起的細(xì)節(jié)似乎已為這次延續(xù)兩年的談判奠定了基調(diào)。那是1982年9月24日,仍沉浸在從馬島戰(zhàn)爭(zhēng)中取勝所帶來的喜悅當(dāng)中的撒切爾夫人,在鄧小平面前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拒絕,在離開大會(huì)堂時(shí),她意外地跌倒在臺(tái)階上,這一情景隨即引發(fā)香港恒生指數(shù)的暴跌。 對(duì)于一位80歲的老人來說,這是一個(gè)過分繁忙、興奮的一年。1月24日—2月10日,他視察了深圳、珠海、廈門經(jīng)濟(jì)特區(qū),并分別題詞;2月11日—16日,他來到上海,說開放得還不夠;2月份還會(huì)見了喬治城大學(xué)的國(guó)際關(guān)系學(xué)者,重申了“一國(guó)兩制”的可行性;3月25日,他再次會(huì)見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示中日必須將兩國(guó)家關(guān)系放在一個(gè)更長(zhǎng)遠(yuǎn)的框架內(nèi);4月18日,他對(duì)英國(guó)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說,在1997年之后,香港的現(xiàn)行制度保持50年不變,6月22日,他又對(duì)香港代表鐘士元重復(fù)了這一點(diǎn);4月18日,他還見到了比他年輕7歲的里根,盡管后者是美國(guó)歷史上意識(shí)形態(tài)色彩最濃重的總統(tǒng),一心相信資本主義必將戰(zhàn)勝社會(huì)主義,但在共同的敵人面前,鄧仍說中美關(guān)系已進(jìn)入了“成熟階段”;他還馬不停蹄的會(huì)見了厄瓜多爾總統(tǒng)、南斯拉夫的共產(chǎn)主義者、巴西總統(tǒng)、緬甸總統(tǒng)、意大利參議院議長(zhǎng)、突尼斯總理……在外交戰(zhàn)略上,他用“反對(duì)霸權(quán),南南合作”逐漸取代了毛澤東“三個(gè)世界”的劃分。 鄧小平用何種方式保持旺盛的精力?1984年見到鄧的聶衛(wèi)平發(fā)現(xiàn)老人仍是個(gè)令人生畏的橋牌對(duì)手,前者說保持健康的四個(gè)原因是:打橋牌、游泳、吸煙、喝酒,像60年前一樣,他仍癡迷于足球比賽。 變化 對(duì)于西方世界而言,1984年充滿著更多的預(yù)言色彩。英國(guó)作家喬治.奧威爾在冷戰(zhàn)序幕剛剛拉開的1948年,描繪了未來世界的悲慘景象,極權(quán)統(tǒng)治使人類徹底失去了自由。根據(jù)這一預(yù)言,蘋果電腦的斯蒂夫.喬布斯制作了轟動(dòng)一時(shí)的廣告。在這一年的2月份,蘇共總書記安德波羅夫去世,他的繼任者契爾年科72歲,比里根與鄧小平都年輕,身體狀況卻很糟糕,越來越多的人將目光投在53歲的戈?duì)柊蛦谭蛏砩希?dāng)時(shí)的職位是蘇維埃外事委員會(huì)主席。比起仍舊“邪惡”而衰敗的帝國(guó)蘇聯(lián),中國(guó)的獨(dú)特生命力令人吃驚。一年后,當(dāng)《時(shí)代》再次將鄧小平評(píng)為1985年的年度人物時(shí),對(duì)他的贊揚(yáng)主要來自于過去6年間中國(guó)社會(huì)已經(jīng)發(fā)生的變化,比起戈?duì)柊蛦谭蛟?985年的戲劇性的動(dòng)作——他同樣提出了“改革,重建”,并出人意料地與里根進(jìn)行裁減核武器的會(huì)談,鄧對(duì)普通公眾的物質(zhì)生活的改變更令人難忘。 大多數(shù)歷史學(xué)家,包括鄧小平自己,都將1979年—1984年視作改革的第一階段,農(nóng)村是它的突破點(diǎn)。而此后,改革開始進(jìn)入城市。“改革不是浪漫曲”,大約在1992年,《中華工商時(shí)報(bào)》的一位名叫胡舒立的記者用這樣的題目回顧80年代末的改革。的確,自從1985年之后,改革最初的生命力正在減弱,而一些弊端則開始暴露。在最初的幾年,除了文革中的造反派,幾乎所有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農(nóng)民收獲到更多糧食,知識(shí)分子擺脫了“臭老九”的身份,工人開始恢復(fù)上班,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復(fù)了工作…… 但在高歌猛進(jìn)的變化中,一些更為復(fù)雜的問題也同樣暴露出來。在1982年7月1日公布的人口普查中,中國(guó)首次超過了10億,通過29臺(tái)巨型計(jì)算機(jī)得出的確切結(jié)果是1,031,882,511。這個(gè)數(shù)字在1964年是6.946億,1953年時(shí)是5.862億,而在1900年時(shí)是4億。鄧小平與他領(lǐng)導(dǎo)的政黨,成為歷史上第一個(gè)統(tǒng)治超過10億人口的個(gè)人與機(jī)構(gòu),而1984年時(shí)全球人口不過48億。 疑慮 中國(guó)社會(huì)不僅如此龐大,而且也如此復(fù)雜。誰會(huì)指望5年的改革會(huì)清除掉所有糟糕的舊遺產(chǎn),每一代人也都有自身無法克服的弱點(diǎn)。治理中國(guó)社會(huì)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必須學(xué)會(huì)在幾線同時(shí)作戰(zhàn),既要面對(duì)封建社會(huì)、半殖民地社會(huì)、極端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留下的遺產(chǎn),也要面對(duì)一個(gè)嶄新的新世界。領(lǐng)導(dǎo)與統(tǒng)治的藝術(shù),在這個(gè)國(guó)家是如此重要。 “打擊經(jīng)濟(jì)犯罪活動(dòng),不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現(xiàn)在是開個(gè)頭。”早在1982年4月10日,鄧小平就意識(shí)到,在改革進(jìn)程中,那些不令人愉快的副產(chǎn)品開始出現(xiàn)了。改革開放最初朝氣蓬勃的社會(huì)空氣開始出現(xiàn)變化,一個(gè)多年來習(xí)慣于“公平”的社會(huì)開始出現(xiàn)明顯的差異化。 “十億人民九億商”是1984年的場(chǎng)景,而到了1985年,人們發(fā)現(xiàn)那些不再進(jìn)入政治舞臺(tái)的高干子弟們通過“官倒”獲得了巨額的利潤(rùn),那些掌握第一生產(chǎn)力的知識(shí)分子們發(fā)現(xiàn),自己的收入還沒有那些小商小販多……與此同時(shí),農(nóng)村的改革也止步不前,產(chǎn)量在1984年達(dá)到高峰后開始下降,而在城市中推行的經(jīng)濟(jì)改革,也沒有最初農(nóng)村改革那樣順利。在企業(yè)改革方案上,“承包制”未能像農(nóng)村“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那樣解決問題,正如日本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小宮隆太郎所說,1985年的中國(guó)根本不存在科斯定義的企業(yè),中國(guó)的現(xiàn)代公司制度一直到1993年才真正建立起來。而那些更為活躍的民營(yíng)經(jīng)濟(jì),總是得不到基本的政策上的幫助。中國(guó)也缺乏一個(gè)能夠承擔(dān)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的新社會(huì)保障體系,在眾多的國(guó)有企業(yè)試圖不再充當(dāng)工人的終身保姆之時(shí),社會(huì)卻不知道如何為那些在工廠中服務(wù)多年、習(xí)慣于一切都由工廠解決的工人提供新的機(jī)會(huì)…… 當(dāng)改革的速度開始放慢,改革者的利益開始出現(xiàn)分化時(shí),各種質(zhì)疑必然會(huì)出現(xiàn)。在改革的最初,人們?yōu)橐稽c(diǎn)點(diǎn)利益而興奮,為一點(diǎn)點(diǎn)自由而倍感快樂,而現(xiàn)在,當(dāng)人們獲得的越多,他們想要的就越多。當(dāng)普通民眾對(duì)眼前迅速變化的社會(huì)風(fēng)氣不知所措時(shí),知識(shí)分子則開始了更為本質(zhì)的追問。當(dāng)鄧小平在1978年表示“科學(xué)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時(shí),知識(shí)分子仍為過去20年的歷史戰(zhàn)戰(zhàn)兢兢,而時(shí)間到了1985年時(shí),知識(shí)分子再次成為中國(guó)社會(huì)一支影響巨大的力量。經(jīng)歷過80年代的中國(guó)年輕人都知道,詩(shī)歌、哲學(xué)與思想對(duì)他們意味著什么。在那個(gè)時(shí)代,有幸上大學(xué)的年輕人是真正意義上的“天之驕子”,他們熱衷于談?wù)撃岵伞⑺_特,就像今天的年輕人談?wù)摫葼?蓋茨與默多克,一本尼采的書可以賣到15萬冊(cè),更為晦澀的《存在與虛無》也能賣到10萬冊(cè)……人們渴望通過新的思想來重新理解生命、愛情和世界,而追問得越多,他們就越發(fā)現(xiàn)需要對(duì)自己的國(guó)家與歷史進(jìn)行重新的思考,那些曾經(jīng)堅(jiān)固的信念都煙消云散了。 在1985年,中國(guó)最流行的一本書是臺(tái)灣作家柏楊的《丑陋的中國(guó)人》。對(duì)于自己身份的質(zhì)疑,通過這本書達(dá)到了頂峰。這本書粗暴與煽情的寫作方式使大多數(shù)讀者相信,中國(guó)人懶惰、自私、不講衛(wèi)生……一直到中國(guó)打開國(guó)門前,中國(guó)人都相信自己擁有著無比的優(yōu)越性——這種優(yōu)越性既來自于傳統(tǒng)的天朝帝國(guó)傳統(tǒng),也來自于我們新的社會(huì)制度。但如今,他們卻發(fā)現(xiàn)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們,卻享受著更好的物質(zhì)條件和更自由的生活。對(duì)于中國(guó)的質(zhì)疑,對(duì)于外部世界的向往,伴隨著改革難度的增加越發(fā)顯著。一位當(dāng)時(shí)的學(xué)生俞敏洪說,他甚至希望飛機(jī)將他空投到美國(guó),多年之后,這位一直未能如愿的學(xué)生創(chuàng)辦了新東方學(xué)校,成為赴美留學(xué)基地。 臨界點(diǎn) 一些最為基礎(chǔ)的東西是不能動(dòng)搖的。鄧小平在提出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同時(shí),也提出了四項(xiàng)基本原則。當(dāng)社會(huì)情緒越來越強(qiáng)時(shí),一些調(diào)整也顯得迫在眉睫。在文革結(jié)束十年后的1986年,對(duì)于毛澤東與文化革命的深入探討越來越多。在這一年9月接受美國(guó)CBS記者邁克.華萊士的采訪時(shí),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還是我們的指導(dǎo)思想”。但在提到當(dāng)前中國(guó)時(shí),鄧小平也相當(dāng)坦誠(chéng)地說:“我們現(xiàn)在做的事都是一個(gè)試驗(yàn),對(duì)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jìn)。既然是新事物,難免要犯錯(cuò)誤。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有錯(cuò)誤就趕快改,小錯(cuò)誤不要變成大錯(cuò)誤。” 事實(shí)上,鄧小平或許比任何人更清楚眼前面臨的問題。面對(duì)一個(gè)日益復(fù)雜的社會(huì),革命思想已不能解決問題,更多的年輕的、擁有更好的職業(yè)技能的官員必須被引入政治系統(tǒng);城市改革中遇到種種困境,多數(shù)都是過時(shí)的體制所帶來的;他也知道,面對(duì)改革停滯所帶來的痛苦,提高速度可能是最好的解決途徑。在1986年6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huì)上,鄧小平說:“政治體制改革同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應(yīng)該相互依賴。只搞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yàn)槭紫扔龅饺说恼系K。”在這一年的11月9日,他還對(duì)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說:“我們?cè)絹碓礁械竭M(jìn)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這種緊迫性到了1987年迅速轉(zhuǎn)化成現(xiàn)實(shí),在那年的十三大上,一些更為年輕的、富有改革意識(shí)、理解現(xiàn)代政治與經(jīng)濟(jì)的官員被引入最高決策層。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發(fā)現(xiàn)5位政治局常委“一個(gè)個(gè)容光煥發(fā),穿著做工很考究的西服,顯得英俊瀟灑”。鄧小平仍未能實(shí)現(xiàn)在這一屆大會(huì)上退隱的愿望,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但仍是國(guó)家軍委主席。與鄧同時(shí)從中央政治局退出的還有另外兩名元老,陳云與彭真,他們都是中國(guó)革命史的某種化身,也共同遭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鄧小平一直在努力說服他的同代人為年輕人騰出空間。 當(dāng)時(shí)間來到1988年時(shí),“價(jià)格闖關(guān)”則成為提高經(jīng)濟(jì)改革速度的舉措。價(jià)格雙軌制所帶來的腐敗與經(jīng)濟(jì)秩序混亂已成為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1988年也是自1984年以來持續(xù)積累的社會(huì)矛盾到達(dá)臨界點(diǎn)的時(shí)刻。激進(jìn)的價(jià)格改革舉措,立刻引起全社會(huì)的恐慌。在因物資匱乏而讓民眾倍感緊張的同時(shí),長(zhǎng)沙的白菜獲得特大豐收,政府為了維持價(jià)格與農(nóng)民利益,出資11萬元收購(gòu)200萬斤白菜倒入池塘中。 由于歷史過分短暫,我們?nèi)圆蛔阋詫?duì)于1989年的混亂作出足夠的評(píng)價(jià)。但不管對(duì)于世界還是中國(guó),1989年的確是一個(gè)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年份,對(duì)于已經(jīng)85歲的鄧小平,這一年則是一個(gè)意想不到的挑戰(zhàn)。 退隱 從1989—1991年,世界重組了。英國(guó)歷史學(xué)家將1914年—1991年定做一個(gè)短暫的世紀(jì),它以一次大戰(zhàn)開始,以蘇聯(lián)解體終結(jié)。在這77年間,意識(shí)形態(tài)的爭(zhēng)端貫穿了整個(gè)世界。也許正如英國(guó)政治學(xué)家約翰.格雷所說,20世紀(jì)的奇特之處在于,人類第一次不是因?yàn)闋?zhēng)奪資源、不是為了宗教,而是為了世俗的信念而戰(zhàn)。 20世紀(jì)中國(guó)歷史的一個(gè)重要特征是,外部因素對(duì)它的作用往往與內(nèi)部因素同樣重要,全球性因素對(duì)于中國(guó)影響非常顯著。沒有1917年的俄國(guó)革命,不會(huì)有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毛澤東自己也承認(rèn),如果中日戰(zhàn)爭(zhēng)不爆發(fā),那么中國(guó)的局勢(shì)會(huì)發(fā)生變化。而中國(guó)在1956年走向一個(gè)激進(jìn)立場(chǎng),也與匈牙利事件與赫魯曉夫關(guān)聯(lián)緊密…… 在1989—1991年之間,中國(guó)再次面臨一場(chǎng)激烈的全球性變革。鄧小平是在1989年11月8日辭去他中央軍委主席職務(wù)的,在這一天下午3點(diǎn),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huì)通過了這個(gè)決議,4點(diǎn)時(shí),他前往人民大會(huì)堂與參會(huì)者照相留念。在他離開大會(huì)堂時(shí),作為新當(dāng)選的總書記,63歲的江澤民一直把鄧小平送到門口,在臨別時(shí)緊握著他手說:“我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正式告別政治舞臺(tái)的時(shí)刻是11月13日,身穿灰色中山裝的鄧小平對(duì)于來訪的日中經(jīng)濟(jì)協(xié)會(huì)訪華團(tuán)的代表說:“(這)將是我會(huì)見的最后一個(gè)代表團(tuán),我想利用這個(gè)機(jī)會(huì),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別。” 但沒人相信,在這個(gè)艱難而動(dòng)蕩的時(shí)刻,鄧小平會(huì)真的離開政治舞臺(tái)。中國(guó)正在陷入少有的孤立狀態(tài),但鄧小平顯然相信,外來者無法了解這一事件的復(fù)雜性。他在10月31日會(huì)見尼克松時(shí)說:“今天來一個(gè)示威,明天來一個(gè)大鳴大放大字報(bào),就沒有精力搞建設(shè)。”而在內(nèi)心深處,西方世界的制裁態(tài)度令他聯(lián)想起中國(guó)與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歷史,在12月1日接見日本代表團(tuán)時(shí),他再次提到了鴉片戰(zhàn)爭(zhēng):“從鴉片戰(zhàn)爭(zhēng)侵略中國(guó)開始,他們傷害了多少人的人權(quán)!巴黎七國(guó)首腦會(huì)議要制裁中國(guó),這意味著他們自認(rèn)為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可以對(duì)不聽他們的話的國(guó)家和人民進(jìn)行制裁。”而中國(guó)人民,“永遠(yuǎn)不會(huì)接受,也不會(huì)在壓力下屈服”。 這也是一個(gè)倍感迷惘的時(shí)刻,原本清晰的道路似乎又失去了方向,甚至一些根本性的質(zhì)疑也開始產(chǎn)生,變化莫測(cè)的國(guó)際局勢(shì)則更增添了這種迷惘與憂慮。從陳獨(dú)秀算起的第一代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人,就是在俄國(guó)革命的鼓舞中成長(zhǎng)的,一直到毛澤東徹底掌握領(lǐng)導(dǎo)權(quán)之前,蘇維埃經(jīng)驗(yàn)都直接影響著中國(guó)的革命。而在1949年之后,毛澤東則干脆直接從蘇聯(lián)復(fù)制了所有可以復(fù)制的模式,在那個(gè)半個(gè)世界都插上紅旗的年代,人人堅(jiān)信東風(fēng)必將壓倒西風(fēng)。即使赫魯曉夫毀滅了斯大林神話,但中國(guó)從來只指責(zé)修正主義錯(cuò)誤,而非蘇聯(lián)模式本身。兩國(guó)領(lǐng)土的爭(zhēng)執(zhí)將原本已受破壞的關(guān)系推到了新的低谷,蘇聯(lián)雖成為“擴(kuò)張成性的帝國(guó)”,但從未有人懷疑過列寧仍是中國(guó)革命的精神導(dǎo)師之一。但現(xiàn)在,那個(gè)一直作為參照系的國(guó)家徹底否定了自己的歷史,他們正在考慮是否繼續(xù)保存存放列寧遺體的水晶棺。一些更為年輕與自負(fù)的理論家們則開始對(duì)于歷史的變遷作出解釋,他們說“歷史已經(jīng)終結(jié)”。 南巡 沒人意料到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之舉會(huì)引發(fā)如此革命性的變化。是的,他仍擁有無人匹敵的影響力。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間,他乘專列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這次后來被廣泛引證與評(píng)論的行程,在最初卻被中國(guó)的新聞界忽略了。在前后六次講話中,鄧小平再次闡述了他的主要主張。他相信衡量國(guó)家與制度是否優(yōu)越的基礎(chǔ)是生產(chǎn)力;他解除了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主義間的界線,說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同樣可以為中國(guó)所用;他從未放棄對(duì)于政治路線的強(qiáng)調(diào),他與毛澤東一樣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而為了確保這一點(diǎn),黨組織與國(guó)家官僚機(jī)構(gòu)必須要高效、年輕化、廉潔。防止和平演變的最好方式,是比對(duì)方做得更好;他也強(qiáng)調(diào)了自己的實(shí)驗(yàn)主義哲學(xué):“不冒點(diǎn)風(fēng)險(xiǎn),辦什么事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每年領(lǐng)導(dǎo)層都要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對(duì)的就堅(jiān)持,不對(duì)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對(duì)于全球局勢(shì),他仍保持樂觀,他相信歷史仍按照馬克思到他那一代共產(chǎn)黨人的預(yù)測(cè)進(jìn)行著,既然資本主義替代封建主義用了幾百年,屢經(jīng)王朝復(fù)辟,那么社會(huì)主義也可能要經(jīng)受暫時(shí)挫折,他說和平與發(fā)展仍是世界主要問題,中國(guó)反對(duì)霸權(quán),并永不稱霸。 當(dāng)然,對(duì)于中國(guó)與世界而言,在這次南巡中,最令他們激動(dòng)的是,鄧小平不僅肯定了改革開放政策,還提出更大膽的號(hào)召。為了表明自己對(duì)于略顯停滯的改革步伐的不滿,他甚至用了他在講話中很少使用的比喻,他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yàn),而“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他也顯露出只有他那一代身經(jīng)戰(zhàn)爭(zhēng)年代人才有的氣魄:“沒有一點(diǎn)闖的精神,沒有一點(diǎn)‘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yè)。” 這是鄧小平最后一次公開的露面,但關(guān)于他的猜測(cè)仍在未來幾年中不斷進(jìn)行,香港的報(bào)紙連篇累牘地試圖從每一個(gè)細(xì)微的信號(hào)里尋找到他的健康狀態(tài)。在他1992年充滿不尋常的朝氣的講話之后,中國(guó)經(jīng)濟(jì)開始進(jìn)入一個(gè)新的高增長(zhǎng)期,而西方世界對(duì)于中國(guó)的評(píng)價(jià)似乎也發(fā)生了顛覆性的變化。一種新的統(tǒng)計(jì)方式表明,中國(guó)不但不會(huì)走向崩潰,而且正在成為世界最為強(qiáng)大的國(guó)家。1992 年11月28日,擁有150年歷史,以理性、冷靜富有洞察力著稱的英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人》雜志上發(fā)表了關(guān)于中國(guó)的16頁(yè)調(diào)查,名為《巨人翻身》。這篇文章第一次用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平均購(gòu)買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實(shí)力,按照這種新模型,鄧小平13年改革的成就是,中國(guó)的國(guó)民生產(chǎn)總值達(dá)到了美國(guó)的2/5、日本的2/3,成為世界第三大經(jīng)濟(jì)體,平均GDP則達(dá)到了2700美元,是當(dāng)時(shí)官方數(shù)字的7倍。在很多時(shí)刻,世界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我們的觀察角度。這篇文章在結(jié)尾寫道:“僅僅一代人的時(shí)間,全世界面臨最重大的問題將是,如何面對(duì)一個(gè)充滿自信、擁有核武器、掌握世界最大經(jīng)濟(jì)體的中國(guó)。”而一片不景氣正包圍著此刻的世界,日本的泡沫破滅了,美國(guó)經(jīng)濟(jì)萎靡不振,俄羅斯與東歐等前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無一不陷入動(dòng)蕩之中。中國(guó)卻開始煥發(fā)無限生機(jī),并且她宣稱自己仍信仰社會(huì)主義。 盡管鄧小平的身體日趨衰弱,他也曾經(jīng)深刻地憂慮將國(guó)家的命運(yùn)與一兩個(gè)領(lǐng)導(dǎo)人的命運(yùn)過于緊密地結(jié)合在一起,不利于國(guó)家的長(zhǎng)期發(fā)展,但他新選定的領(lǐng)導(dǎo)集體卻正在獲得越來越高的權(quán)威性。1992年,朱镕基從上海來到北京,他與江澤民有過不短的合作經(jīng)驗(yàn),他將主管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工作。 1993年、1994年,鄧小平的文選再次增訂出版,它的印量沒有毛選那么大,卻同樣引起了購(gòu)買的熱潮。在回顧自己的漫長(zhǎng)而坎坷的一生時(shí),鄧小平也看著自己過去的朋友與敵人中最后一批幸存者紛紛離去。1992年,李先念與聶榮臻去世,1995年,陳云去世,自延安時(shí)期以來,他一直是中共經(jīng)濟(jì)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1978年時(shí)支持鄧小平的改革,并在1980年代晚期,開始持不同意見。而在1991年時(shí),被鄧小平打到零分以下的江青也在醫(yī)院中自殺,據(jù)說在生命的最后時(shí)光,她常常閱讀毛澤東的著作,并在床頭擺放著她與毛澤東的合影。 鄧小平的遺囑顯示了他多么盡力地去遵循自己的承諾,他竭力去除個(gè)人因素對(duì)于中國(guó)社會(huì)過大的影響力。他的遺體被火化,骨灰被拋灑在中國(guó)大地上。他也不用像毛澤東那樣擔(dān)心他的遺產(chǎn)被篡改,他的繼任者繼續(xù)推進(jìn)了他經(jīng)濟(jì)改革的政策,在他去世8個(gè)月后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繼5年前破除計(jì)劃經(jīng)濟(jì)迷信之后,又破除了所有制的迷信,一些更為敏感的旁觀者發(fā)現(xiàn),在這次大會(huì)上,再?zèng)]有一名經(jīng)過長(zhǎng)征時(shí)代的老代表了,一個(gè)新時(shí)代開始了。 發(fā)展 對(duì)于鄧的遺產(chǎn),我們今天仍持有爭(zhēng)議。沒人會(huì)否認(rèn),在經(jīng)濟(jì)高速增長(zhǎng)的背后,也同樣蘊(yùn)涵種種缺陷。一位社會(huì)批評(píng)家說我們正在面臨“現(xiàn)代化的陷阱”。中國(guó)正在變成一個(gè)失去平衡的社會(huì);腐敗日益猖獗,并有可能形成制度性的;這個(gè)國(guó)家正在失去靈魂,變成赤裸裸的消費(fèi)主義與物質(zhì)主義,對(duì)權(quán)力與金錢的崇拜,而在世界歷史范圍內(nèi),我們也很少見到中國(guó)20世紀(jì)90年代這一盛況——知識(shí)分子如此徹底地撤離公共生活……而最令人擔(dān)心的是,占據(jù)這個(gè)國(guó)家70%以上人口的農(nóng)民,仍未能尋找到有效地參與這個(gè)國(guó)家進(jìn)程的方式,這也是困擾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所有中國(guó)政治家的問題。 與此同時(shí),一些過去常常被我們忽視的問題也正在妨礙這個(gè)國(guó)家的繼續(xù)發(fā)展。艾滋病、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性與日益嚴(yán)重的男女比例失調(diào)正在成為中國(guó)發(fā)展面臨的新障礙。我們已擁有超過100萬的艾滋病人,這個(gè)人數(shù)可能在10年后超過1000萬人;中國(guó)2/3以上的主要城市都有嚴(yán)重的缺水問題,被污染的空氣、河流與森林已成為生活的一個(gè)主要組成部分;由于傳統(tǒng)觀念的支配,男女的性別比例已達(dá)到116:100,人們或多或少會(huì)意識(shí)到,20年后當(dāng)超過3000萬的青年男子無法尋找到婚姻愛情時(shí),可能會(huì)給社會(huì)帶來怎樣的慌亂。 但即使如此,我們?nèi)砸姓J(rèn),鄧小平可能是20世紀(jì)所有主要的政治領(lǐng)袖中爭(zhēng)議最少的一位。比起過去150年的劇烈動(dòng)蕩,1979—1997年的中國(guó)歷史像是一個(gè)意外的插曲,它沒有全國(guó)性的混亂與精神迷狂,中國(guó)故事的主題不再是對(duì)抗侵略、軍閥混戰(zhàn)、階級(jí)斗爭(zhēng)、暴力活動(dòng),而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如何提高每個(gè)普通人的物質(zhì)生活水平。中國(guó)不僅擺脫了孫中山時(shí)代面臨的全面性危機(jī),甚至在外部世界也逐漸獲得尊敬,西方世界多年以來談?wù)撝袊?guó)即將崩潰的習(xí)慣到了20世紀(jì)結(jié)束時(shí),突然全部轉(zhuǎn)變?yōu)椤爸袊?guó)崛起”與“中國(guó)威脅論”。中國(guó)再次成為很多發(fā)展中國(guó)家試圖追隨的楷模。在國(guó)家統(tǒng)一問題上,她解決了香港與澳門的回歸問題,盡管臺(tái)灣的情況沒有她最初預(yù)料的那樣樂觀。 大歷史 中國(guó)的故事依舊在繼續(xù),但她已變得日益復(fù)雜。在2001年社科院發(fā)布的一份報(bào)告中,社會(huì)學(xué)家們發(fā)現(xiàn)中國(guó)社會(huì)已至少可以劃分為十個(gè)階層。很顯然,不管是列寧所說的工人階級(jí),還是毛澤東所依靠的農(nóng)民都不足以概括中國(guó)。當(dāng)孫中山去世時(shí),是廣播與報(bào)紙通報(bào)了這一消息,而當(dāng)鄧小平去世時(shí),人們通過電視轉(zhuǎn)播與互聯(lián)網(wǎng)了解這一情況。當(dāng)鄧小平出生時(shí),鋼鐵、石油、海軍力量是一個(gè)國(guó)家強(qiáng)大的標(biāo)志,而現(xiàn)在人們談?wù)摰氖请娮討?zhàn)爭(zhēng)。與前幾位政治領(lǐng)袖不同,鄧小平最后20年身處的時(shí)代,或許面臨更為根本的社會(huì)性變革——全世界正在完成由工業(yè)社會(huì)向信息社會(huì)的轉(zhuǎn)移過程中,國(guó)家主義徹底失效了,它越來越不可能控制個(gè)人的生活。也因此,鄧小平時(shí)代在20世紀(jì)最與眾不同之處是,國(guó)家與社會(huì)的重心重新向社會(huì)一方傾斜,“解放思想”實(shí)質(zhì)上就是對(duì)個(gè)人自由的強(qiáng)調(diào)。而在此之前,不論是孫中山還是毛澤東,都強(qiáng)調(diào)將國(guó)家置于一切個(gè)人之上,政治組織隨時(shí)可以進(jìn)入社會(huì)每一個(gè)角落。 也是在20世紀(jì)最后20年,一種新的歷史觀逐漸引起了更多的注意力。黃仁宇稱之為大歷史,他相信只有將20世紀(jì)放在一個(gè)更大的語境內(nèi)來看,才會(huì)理解中國(guó)出現(xiàn)的種種不可思議的悲劇性事件。那些劇烈的征戰(zhàn)與內(nèi)亂,都是在為中國(guó)向一個(gè)通過數(shù)字來管理的現(xiàn)代國(guó)家的演進(jìn)做準(zhǔn)備。如果黃先生對(duì)于數(shù)字管理的過分迷信有失偏頗,那么另一位政治學(xué)者的描述或許更為可信。于1999年去世的鄒讜的父親是國(guó)民黨元老,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他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后來前往芝加哥大學(xué)留學(xué)并任教。他在1980年代曾寫道:“二十世紀(jì)以來,中國(guó)的確遇到許多挫折;不過從長(zhǎng)遠(yuǎn)的歷史眼光來看,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國(guó)二十世紀(jì)所要解決的問題,至少相當(dāng)于西方從文藝復(fù)興以來幾百年所要解決的問題,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經(jīng)濟(jì)發(fā)生最大變化的時(shí)期進(jìn)行的。所以,中國(guó)二十世紀(jì)所經(jīng)歷的挫折和困境,雖然不能說完全避免,起碼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對(duì)于中國(guó)現(xiàn)在所面臨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有這樣一個(gè)遠(yuǎn)大的歷史眼光,不然就會(huì)過分估計(jì)了失敗,對(duì)前途產(chǎn)生不必要的悲觀情緒。” 2003年10月23日,宋美齡在美國(guó)去世,她的姐姐宋慶齡早在1981年就已離世。在某種意義上,她的離去宣布了20世紀(jì)的正式終結(jié),所有歷經(jīng)那些浩劫與慘痛、筑造那些光榮與夢(mèng)想的巨人式的人物都已告別。“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大約在1917年,孫中山寫下了這句話。歷史學(xué)家發(fā)現(xiàn),盡管潮流常會(huì)有變化,但貫穿一個(gè)世紀(jì),一些基本的趨勢(shì)仍很顯著,技術(shù)變革的速度加快,世界變得更加民主與自由了,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是可以不斷維持的。我們做到了一些,還有更多的沒有做到。 對(duì)于歷史,我們?nèi)菀追傅腻e(cuò)誤是,我們忽略掉當(dāng)時(shí)的情景,而一廂情愿地按照現(xiàn)在的角度來思考。對(duì)于所有偉大的變革者而言,忽視他們所處的時(shí)代,凌空談?wù)撍麄兊某删投际强尚Φ摹膶O中山到鄧小平,從每一個(gè)人身上,我們都能歸納出無窮的結(jié)論,給他們的遺產(chǎn)簿上增加源源不斷的頁(yè)碼。但不要忘記英國(guó)作家阿多斯.赫胥黎的警告:“不過一兩代人的工夫,那些標(biāo)新立異的思想就變成了正統(tǒng)僵化的說教。”這些偉大人物最重要的、永不枯竭的遺產(chǎn)就是,他們?cè)诿鎸?duì)不同的困境時(shí),都不畏懼傳統(tǒng)的成見,愿意嘗試新的道路,當(dāng)他們開始行動(dòng)時(shí),他們都很年輕,他們可能所知不多,但他們心中都被一些熱忱的信念所鼓舞著,他們知道到達(dá)彼岸的旅程并非一帆風(fēng)順,但他們?cè)敢庀嘈抛约夯蛘咦约旱暮蟠K有可能到達(dá)。他們當(dāng)然也會(huì)、甚至經(jīng)常犯錯(cuò)誤,但他們比任何人都愿意承認(rèn)自己的錯(cuò)誤。正如鄧小平所說的:“在這場(chǎng)革命中,我們是在不斷解決新的矛盾中前進(jìn)的。”(完) 蘋果電腦 |
| 新浪首頁(yè) > 財(cái)經(jīng)縱橫 > 隨筆砸談 > 正文 |
|
| ||||
| 熱 點(diǎn) 專 題 | ||||
| ||||
|
|
新浪網(wǎng)財(cái)經(jīng)縱橫網(wǎng)友意見留言板 電話:010-82628888-5173 歡迎批評(píng)指正 新浪簡(jiǎn)介 | About Sina | 廣告服務(wù) | 聯(lián)系我們 | 招聘信息 | 網(wǎng)站律師 | SINA English | 會(huì)員注冊(cè) | 產(chǎn)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